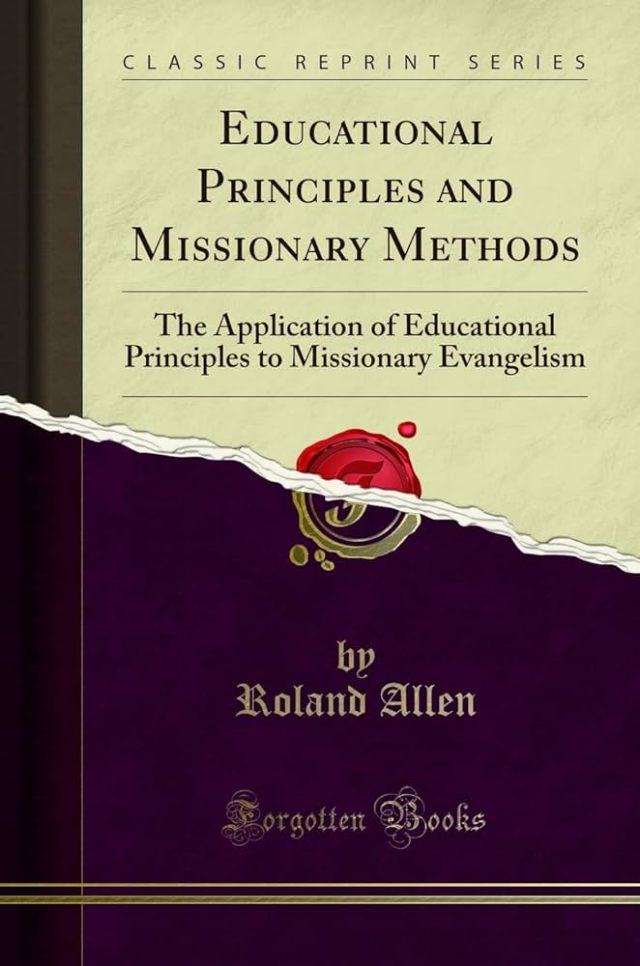第四章 教育的终结
在普遍的思想和语言中,教育的终结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达到的,当孩子长大,脱离了家长和教师的管教,预计他能自己指导和控制自己的生活。这个终结是在一定的身体和心理发展阶段达到的,而这个阶段是由父母的社会、道德和心理标准所决定的。当一个孩子达到这个阶段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就已经受过教育了。因此,人们说一个孩子“完成了”他的教育:“当他的教育结束时,”他们说,“他将进入这个或那个职业。”人们说某人“在某某学校接受过教育。”在这样的语言中,很明显,教育被看作是一个适合儿童的临时性训练,而它的终结是当孩子成为成年人时。
这种对教育终结的看法是非常自然的,但它极其片面且危险。
(1) 它助长了那种令人厌恶的习惯,把童年仅仅视为成年生活的准备。将童年视为仅仅是为其他事情做准备,这对人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罪过。孩子有权利作为孩子存在,正如成年人有权利作为成年人一样。人类并不是仅仅为了成为成年人而存在;他们是孩子,是为了能够做孩子。把整个人生都视为只是为另一种生活做准备,这与把童年视为只是为成年生活做准备一样不合理。我们都知道把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生活当作是仅仅为其他生活做准备的危险性;但同样危险的是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视为仅仅为其余部分做准备。事实上,当我们与我们期待的更丰盈的生命进行比较时,我们所称之为成年期的阶段,其实只是一个童年。把它当作终结显然是荒谬的。
(2) 它鼓励我们养成一种有害的习惯,即认为童年是人类无法自我指导的时期。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根据我们的经验,只有那些存在缺陷或教育不良的孩子,才会让我们觉得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或引导自己的进步。只有教育不良或有缺陷的孩子,才不能被信任独立完成任何事情。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能够做很多事情。他们会走路、说话、玩耍。如果他们学会了阅读,他们能够正确而有智慧地阅读,并从阅读中学到很多东西。他们能够独立做许多有助于智力、身体和道德进步的事情。以一种非凡的程度,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指导自己的进步。孩子们的能力与成人相比,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相较于我们所知道的成年人的能力,孩子的能力在比例上要大得多。只是由于一种奇怪的盲目自豪感,我们才认为成年人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与小孩子相比是更大的。成年人能控制自己的四肢吗?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不舒服的抽搐、颤动和其他奇怪的行为,令我们的朋友感到困扰、恼火或好笑?成年人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吗?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漫无边际的杂念的困扰?成年人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吗?那为什么我们会做出许多事前不愿做、事后又感到后悔的事情?我们是否没有被一系列习俗和外部控制所束缚,无法接近自由行动?如果孩子们在他人的控制下行使他们的自由,那么成年人也是如此;如果成年人有任何行动自由,任何自我指导的能力,那么孩子们也是如此。
(3) 将童年视为人类无法自我指导的时期,将教育视为仅仅是为成年的准备,将教育的终结视为孩子成为成年人的固定时刻,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并纵容了一种非常糟糕的教育形式。
(a) 由于童年被视为孩子无法自我指导的弱势时期,因此教育者,无论是父母还是教师,常常会陷入过度指导的严重错误。给予的帮助过多;为孩子做了一些他完全可以自己学会做的事情;结果是,孩子没有学会自己应该能够做的事情,而是学会了依赖他人的帮助。他没有被允许独立做他能做的事,结果就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谁不知道那种只能在别人看着并且有长辈的道德支持和鼓励下做得非常好的孩子?谁不知道那种只能在父母或教师的支持和鼓励下表现得非常好的孩子?
(b) 由于教育的终结被看作是一个在特定时刻必须到达的固定点,父母和教师常常会表现出不必要的急躁。随着孩子长大,当他们看到孩子接近“教育的终结”时,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孩子早期教育中所给出的依赖性培养的恶果。他们看到孩子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无法像他们现在知道的那样引导自己的进步,在沮丧和急躁的交替状态下,他们试图在孩子的最后几年里,把自我控制的训练塞进来,而这本该在婴幼儿期打下基础。
有一种看待教育终结的观点,避免了这些危险。在这种观点中,教育的终结并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达到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如果说教育有终结的话,它是在每个人生阶段和每个时刻都有一个终结。终结是在人的行为能够在适合其年龄、状况和环境的限制下,自我控制并引导其进展时达成的。当婴儿能够控制言语器官,以适合其年龄的方式表达相应的思想,并能利用言语促进自己的知识进步时,他就达到了教育的终结;当一个男孩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在适合他年龄和状态的条件下集中注意力,并利用这种注意力促进自己理解力的提升时,他就达到了教育的终结。如此等等。每个阶段的教育终结,都是在这个阶段里获得控制和引导自己进步的能力。
因此,所有教育的真正标准就是学生在自己的发展阶段能够自我指导行为的能力。这个能力一旦获得,未来的进步就依赖于它。如果孩子没有获得这种能力,那么当教师的指导被移除时,他很容易陷入各种错误,或者停滞不前,失去他所学到的所有或大部分知识。如果成年人没有学会在现有条件下适合他们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引导,那么他们未来进步的希望几乎微乎其微。没有以获得这种能力为终结的教育显然没有真正的终结;它只是停止了,它已经失败了。
其次,这就意味着教育的正确方法是一种逐步转移的方式。学生必须学会独立做那些最初只能在指导下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控制必须不断地从教师转移到学生。突然的转移是致命的,我们常常能在那些突然摆脱父母和教师控制的年轻人身上看到这种情况。转移必须是渐进的,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控制的转移。这种转移不能通过几节“结束”课程来完成。一个长期依赖、长期在严格监督下的孩子,无法通过几节特别课程学会自我控制和自我指导。近年来,我们愈加意识到,这种能力只有在作为孩子教育最初步骤的一部分时,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控制的转移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的方法,如果教育要达到其终结的话。
现在,对于这两种教育终结的观点,我们在传教领域中选择了哪一种,已经不成问题。我们接受了那种错误的教育终结观点,将它视为一个必须达到的固定点,并且将教育视为仅仅是为这一终结做准备。
常见理论是,在所有的传教工作中,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信徒完全依赖于传教机构。在这一阶段,他们受到管理,所有的教育都是通过指引进行的;他们完全无助,无法自理;必须通过规章制度来约束他们。在这个阶段,法律和习俗必须由外部权威强加,并且信徒必须按这些法律和习俗进行训练。传教机构是父母,信徒是婴儿,唯一的美德是服从。
第二个阶段是,开始出现土著教会的希望。婴儿开始表现出他未来可能成为成年人的迹象。在这个时候,传教机构像一个过度宠爱孩子的父母,开始发现控制孩子日益增长的精力变得困难,孩子也开始表现出某种反抗约束的迹象。未成熟的土著教会和传教机构并行不悖,两者之间的关系难以调整。这是我们传教工作普遍已达到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假设是土著教会完全学会了法律和习俗的训练;它将达到成熟;它将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到那时,我们将完成它的组织结构。我们将任命主教并建立主教会议,教会最终将独立完整。传教机构将退役,或者仅仅作为友好的顾问和帮助者。
这个理论显然基于一种将教育的终极目标视为在某一阶段达成的固定点的教育观念,在这一阶段之前的各个阶段只是为达到这一目标做准备。这同样是对儿童的权利和儿童教育的真正意义与目的的否定。它假设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到达成年,而成年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它认为,一个信徒在学习了我们的美德并以我们实践的方式进行宗教仪式之后,便达到了成年;而一个教会当它能够维持和管理一个与我们相似的系统和组织时,也达到了成年。
它引发了同样的恶劣教育方式。在早期阶段,我们受到同样过度指导的诱惑。我们无法等待他们自己去做任何事情。即便他们有一点努力,也显得对我们而言是徒劳和误导的。我们急于为他们做一切,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所有外部条件,就像他们完全无法独立做任何努力,除非他们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孩子气的帮助。通过为他们做事,而他们只需接受我们所做的并服从跟随我们,我们成功地表现出了一种达成的假象。
在后期阶段,依然会出现同样危险的不耐烦,急于看到他们开始表现出自己做事情的能力。它依然是我们要他们做的事情,我们的组织必须被他们使用。我们就此努力推动他们,强迫他们担任一些权威职位,强加某种自治方案,要求他们提供更大的支持,或者,按照我们的说法,是自我支持。我们为他们的滞后感到忧虑,或者吹嘘他们在应对我们要求时所作的努力。目标始终在我们眼前,作为一个需要达成的终极目标。我们总是在为这个目标做准备。而我们忘记了即时的目标,那个唯一能带来真正成熟的目标——他们当前所处阶段的行为规范和自我进步的能力。
即便在那些承认变革必要性的人当中,仍然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表面上的变革就足够了,认为长期的依赖训练可以在几年内扭转过来,认为独立训练可以作为一种“完结”课程来处理。
有一种想法认为,早期的信徒和婴儿教会可以被允许并鼓励依赖外部援助一两代人,然后引入组织来训练他们独立。于是我们引入财务委员会和评估制度来训练信徒自我支持,教会委员会来训练他们自治,传教社会来训练他们自我扩展。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任命土著副执事和祝圣土著主教,指引他们未来的自主之路。
这确实是对改革必要性的认同。我丝毫不贬低这些措施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对土著基督教社区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我坚信,正如现代欧洲教育家被迫回到最初的教育起点,寻求坚实的基础一样,我们也将被迫回到起点。控制的转移是如此根本,以至于它不能在后期阶段才开始。它不能从顶部开始;必须从底部开始逐步落实。它不能作为建筑的最后一块石块来增加:它是所有基础的基石。终极目标必须在开始时就隐含其中。
仅仅找到一些特殊的个体,我们可以任命为副执事和主教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一个已经准备好并且能够向前迈进的社会,一个能够在现有阶段指引自己进步的教会。所需要的不是在教会委员会中表达的自治,而是一个已经学会在当前阶段指引自己进步的人民。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传教会的建立——这意味着人民还不是传教士,必须加以培养——而是一个已经学会自发地以适合他们现阶段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传教热情的人民。所需要的不是一些加上去的东西,虽然它们可能显示出超越当前阶段的达成,而是通过真实的达成来取得最终目标:在当前阶段能够指引自己进步的能力,以适合该阶段的方式。
这些旨在纠正过去过度指导的恶果的努力,本身也带有相同的恶性。这些努力仍然是自上而下强加的。正如我们最初将所有的权威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从上而下指导人民,因为我们轻视婴儿阶段的无力一样,现在我们也将独立的形式强加给他们。这些现代化的变化就像我们早期所做的那样,是由我们来实施的。我们说,“你们必须独立,你们必须自给自足,自我管理,你们必须有传教社会”,正如我们之前说“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的财务、组织和传教工作的指导。”即使今天,我们任命土著副执事和主教,建立教会委员会,鼓励传教社会,我们通过极其小心的谨慎,设法为他们提供每一项预防措施,以防他们做出我们不赞成的事。这既是失败的 confession,也是承认旨在纠正失败的计划与旧有方法的相似性。
此外,这些努力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去教育中真正的错误。因为我们采用这些方案来教授信徒自我指导,作为一种“完结”课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了那种导致这些晚期努力出现的错误教育观念。我们依然认为教育的终点是一个固定的点——达到成年,就是我们所享有的成年。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准备那个时刻而进行的绝望尝试。终极目标不能在最后一刻凭空获得,我们必须回到最开始的地方,或者尽可能回到起点,重新开始并设定新的目标——不是达成我们贫弱的成年,而是每个人、每个教会根据他们实际所在阶段应当达成的目标:自由和自我引导。
这是一项深远的研究机会。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危险——大规模的教会完全依赖我们,开始感到他们的依赖变得苦涩,但他们还没有学会指引自己的道路。世界的福音传播被这一点阻碍远甚于缺乏人力或资金。
如果我们要找到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我们必须努力更深入地理解教育的最终目标,并认识到这一观念对我们与信徒特别是在接触初期的互动至关重要。对我们来说,终极目标是即时的,而不是遥远的。在每一堂课中,我们都必须达成目标。因此,圣保罗的信徒们被看到已经达到了目标。他们听见了,理解了,付诸实践,按照所给予的光明生活。他离开了,他们继续实践他所教导的内容。他们犯了错误,堕入罪恶,被假教师欺骗;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已经通过他的教导达成目标的事实。
对我们来说,所有的教学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这个目标必须是立刻就能达成的,这个目标应该是具备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规范他们自己的宗教生活,并引导他们自己进步。这必须是使我们的学员暂时脱离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力。每一堂课的目标必须是朝独立迈进的一步。是否达成目标的真正标准是老师的离开。这是我们应该在每一堂课后所应用的标准。教导然后离开是黄金法则。然后,通过仔细观察和实验,我们可以逐步发现最好的方法或程序顺序。
我们心中如果能强烈根植这一观念,将产生奇妙的效果。即使我们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为某一特定的传教区制定出与一些欧洲最好的家庭和幼儿园相比的教学方法,即使我们为每一步的无知而感到沮丧,但仅仅因为我们在努力追求这一目标,并且致力于教育我们的信徒规范他们自己的宗教生活并引导自己进步,这一努力将被他们深切感受到,并产生极其有益的结果。通过不断的实验,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种方法。
这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我们决定探索我们的信徒可以真正为自己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比我们预想的能够做得更多;当我们发现了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何为他们打开前进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他们肯定能够为自己做,因为他们通过今天所做的事情,所获得的经验本身将为他们准备好明天应做的事。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当前阶段达到了教育的最终目标,这本身就是我们在下一个阶段,无论它是什么,都会达成目标的保证。
本文译自”EDUCATIONAL PRINCIPLES AND MISSIONARY METHODS” by Roland Allen. 仅作个人学习分享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