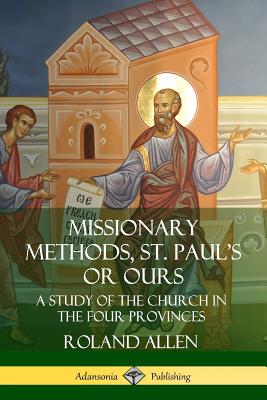本文译自书籍 “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A STUDY OF THE CHURCH IN THE FOUR PROVINCES, BY ROLAND ALLEN(FORMERLY MISSIONARY IN NORTH CHINA)
十四、后记:当代的对比
为了增加我在前几页中所提出论点的深度和现实感,我将通过现代生活中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设想了两个人在相似的环境下工作。我首先做了一张合成照片。所有细节都取自生活,但没有一位传教士提供所有的细节。所得到的画面因此是虚构的,但我认为人们会立刻认出这代表了一种真实的类型,而不是一种罕见的类型。第二个例子则不是合成的。它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实际经历;故事几乎完全摘自他工作日记中的内容。
第一部分
这位传教士是一个好人,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他真诚地希望建立起本地教会。他在一个大的地区工作,努力完成两三个人的工作。
他首先建立了学校和教堂。他明白,除非他所皈依的孩子们能够接受一些教育,否则他们无法按他期望的方式进步。他看到了他们父母的贫困,无法为教育做出太多贡献,甚至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也几乎无法承受失去孩子的帮助。因此,他不得不寻找其他支持来源。他向各种团体求助,写信,争取家乡朋友的支持,筹集捐款。他不断劝诫并教导他的皈依者,直到他们开始明白,帮助教育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而且他们知道他是为了他们的福祉,因此愿意帮助他开展任何他开始的工作。于是,在他们的贫困中,他们捐出了钱和劳力,最终建起了学校——村里的小学和一个位于中心站点的中学。学校建在传教区的土地上,属于传教区,传教区提供了教师,并依赖教师保持教会成员对学校的兴趣,并鼓励他们送孩子上学。
同样,传教士为他的人民建了教堂。他说,如果集体教会生活要成为现实,皈依者必须拥有教堂。这些教堂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且需要不小的劳动力和焦虑。在某些情况下,他实际上亲自参与了建造工作;在所有情况下,他都进行了细心和持续的监督。他非常担心他的建筑应当尽可能好,并且尽可能像一座教堂。不仅是外观,他还力求内部的设备既要好看又要完善。通过他在英格兰的朋友们的帮助,他成功地为其中一些教堂提供了钟和风琴。他引进了穿白袍的合唱团;他还促使英格兰的女性协会为他寄来了祭坛布和祭坛帷幔。他指导他的人民使用《祷告书》,并通过持续的努力教会他们有序地进行礼拜。他甚至让他们学唱《古代与现代圣歌》的翻译版,因为他们是音乐人——尽管这些曲调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翻译也不完美,有时几乎让他们无法理解。因此,他的教堂礼拜成了来自英格兰的访客们的赞赏之处。
然而,他并不完全满意。教堂和学校都需要持续的监督。皈依者往往有这样的倾向:一旦他的激励性存在被短暂撤走,事情就开始衰败。白袍变脏破,祭坛布被虫蛀,建筑物本身也被忽视。人们有时会开设非正式的礼拜,唱本地人写的、用本地旋律演唱的圣歌,忽略了每日的公祷。他感到气馁。他意识到,要建立起一种他理解的体面的、有序的礼拜习惯,需要很长时间。他的皈依者已经慷慨捐款,他曾夸赞他们的自给自足。然而,他们似乎并未将这些成果视为他们自己的。他们似乎没有热情地去吸引那些未信的邻居加入教会。
因此,他热烈欢迎一个教区计划,目的是建立本地的教会委员会,因为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人民能够学会更聪明、更积极地参与教会管理。他立即开始实施这个新方案。他指示本地牧师和助手们去组织委员会选举。一开始,牧师和人民都不理解这一做法。他们只看到这不过是获取资金的一个新方式。当地的一位牧师这样向一位陌生人描述了他的经历:“人们走到我们面前,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想被咨询。传教士是我们的父母。他们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告诉他们:‘传教士安排的,他们希望你们这样做,他们认为这能让你们在事务管理上更有能力,并使你们更具自给自足的能力,我们必须这么做。’然后他们做了。渐渐地,他们发现被咨询是有趣的,感觉到自己变得重要起来。他们不仅捐款,还在一定范围内管理了这些资金。确实,传教士审查了所有的账目,并强烈反对任何未经授权的开支,但仍然,在他的指导下,他们确实管理了一些资金。他们也学会了批评资金的使用。他们知道从传教区得到的钱很多,他们推测传教士管理着比他们所知道的更多的资金。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捐了多少钱。他们知道传教士夸耀他们的慷慨。他们也开始感觉到自己做了很多。对于外人,他们的第一句话常常是谦虚的夸耀自己在自给自足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第二句话则暗示他们从传教基金中得到的资助并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多。”
当然,他们没有被允许在自我治理方面走得太远。传教士认为,如果那些还没有学会走路的人被允许跑步,那将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所有的会议都是传教士所认为应该做的事,而不是自由提议和讨论。“如果他们做了自己想做的事,那我该怎么办?”传教士说,“如果他们想做我不赞成的事情呢?我必须把事务的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点得到了本地牧师的大力支持,他们完全独立于自己的会众。传教士希望任命一位特别的教理教师,专门负责教导孩子们——一种专为儿童设计的传教方式。在一个牧区,牧区委员会没有看到这一计划的智慧或必要性,但传教士表达了对这一计划的支持,于是牧师按照传教士的意见执行了这项计划。牧区委员会拒绝支持这一计划,结果牧师否决了他们的决议。地区委员会在传教士的主持下通过了这一提案。计划得以实施。牧区委员会此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由于这一提案绕过了他们,他们不同意这一计划,因此他们不会为该计划提供任何资金。牧师再次否决了该决议,并从教会基金中支付了费用。尽管委员会成员并不总是与传教士意见一致,因此不得不被推翻,但他们的存在的确鼓励了皈依者的自给自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教会了他们自我治理的艺术。传教士对此非常满意。他真的希望他们学会管理自己的事务;只是他认为在早期阶段,他们不能允许自己走错路。
同样,在纪律方面,他非常希望教育人民。他并不认为仅仅依靠白人传教士的命令来行使纪律。他认为人民应该被代表出来。在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中,他会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如果案件有任何特殊的难度,他会亲自下去并坐在调查委员会上。毫无疑问,公正得到了执行。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基督徒往往在传教士在场时拒绝款待那些被逐出教会的人,而在传教士不在时又接待他们。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动的重大责任。如果有人建议,如果本地的教会在最初单独行动,事情可能会不同,回答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本地委员会宽恕了道德上的过错,那就太可怕了。”
如此这般,传教士在治理他的皈依者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精力和成效,因此他被任命为教区大会的秘书。在那里,他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能力。只可惜,他的语言能力不足以迅速写作或翻译论文,因为大会的规定是所有事务必须用本地语言进行,但这个问题通过放宽规则得以解决。幸运的是,几乎所有的本地会议成员,或者至少是有影响力的成员,都能说英语;演讲者在特殊场合可以使用方言,以便那些听不懂其他语言的人能理解。然而,即便如此,传教士和他的同伴们还是感到有必要将事务的管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天,他的一个教区成员在大会上提议,将一栋原本为外籍传教士建造的住宅,改建为该地区的中学。这是传教士完全反对的提案。这直接冲击了他在中心车站亲自管理的中学的地位。他站起来反对这个提案。然而,他无法说服提案者,后者再次站起来,开始为他的计划发表长篇演讲。提案者非常急切,因为他是这个地方的本地人,而且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教会成员。于是,传教士打断了他,果断地结束了他的演讲:“反正,这是我们的建筑,不是你们的,我们不会让你们把它用作那个目的。”
第二部分
第二位传教士负责的地区要小得多。他开始时向他的主教提出请求,希望撤回通常为他传教站提供的津贴。他希望自己和三位本地教理教师的工资由他们自己领取,但不再需要其他资助。“如果,”他说,“我们需要钱做某些事情,我们会申请,并说明我们能做什么,计划做什么,和需要什么帮助;如果您认为合适,可以从传教资金中提供帮助。我会确保工作完成,并在工作完成后告知您。但我不打算保留任何传教账户,因为我从不把传教资金放在自己手中。”
根据主教的指示,并作为教区计划的一部分,他让四个小教会选举出一个委员会,并利用这个委员会。如果任何教会需要做什么事情,要么是会众自己发现需求,要么是传教士提出需求,直到会众感受到这个需求。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需求时,会众会集会讨论(如果传教士在场,他就在;如果不在场,他就不在),并考虑他们能做些什么来满足这个需求。如果他们能够满足,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当传教士来巡查时,他们会自豪地展示他们的工作,并得到应有的赞赏。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就会指派代表去教区委员会请求帮助。代表们会出现在委员会面前,陈述情况,说明地方教会能承诺多少费用,还需要多少。
教区委员会手中有一小笔基金,由财务主管管理。如果委员会批准了计划,就会投票批准资助。如果这笔资助不足以满足需求,传教士就会将问题报告给主教:“地方教会想做某些事情;它愿意出多少资金;教区委员会愿意出多少资金;他们仍然需要多少。我认为地方的捐款足以证明人民对于这项工作真的很重视(或不重视,视情况而定)。我认为教区委员会的资助足以证明委员会一致同意应该做这项工作(或不做,视情况而定)。您能补充差额吗?”如果资金获批,它会交给教区委员会,后者将其与自己的资助一起交给地方教会,工作便完成了,事情就此结束。
最初,这让人们感到十分惊讶。一所地方教会想要一所学校。人们请求传教士在他们的村庄里建立一所学校。他们说:“我们想要一所学校。” “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办一所?”传教士回答道。他们惊讶极了。“什么?”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办一所学校?” “你们的异教邻居是怎么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他们自己凑钱,邀请老师。” “那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 “但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传教士总是安排老师。” “我不能为此负责。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必须给你们找老师。我没有老师,你们有。你们中间没有人能教几个小孩子读书、写字和背诵教义吗?” “但是我们可以做这个吗?” “当然,为什么不可以?” “那我们该怎么付老师的工资?” “听着,”传教士说,“你们去考虑一下,商量一下,看你们能做什么,然后来告诉我。如果你们有困难,我或许会从我自己的口袋里给你们一点捐款。”(这里他犯了个错误;他应该告诉他们向教区委员会报告,但这是他的第一个案例,他自己也没完全考虑清楚。)于是他们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就开始了。这个项目花费了传教士大约1英镑。
他很少谈论教会、身体或合一;
他总是以教会、身体和合一是真实的事实来行动。他把教会当做教会来对待。他拒绝把教会的个别成员当作单纯的个体。在他到达这个地区之前,曾发生过严重的纷争和扰乱,极大的迫害和痛苦。出于对生命的恐惧,一些基督徒曾经背离了信仰。他们虽然没有像我所知的那样,行异教的仪式,但他们不来教堂;他们也不愿意公开和基督教会聚集在一起。传教士并没有去找这些人。他专注于教会。他提醒教会,这些离教的基督徒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如果继续未悔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提醒基督徒,他们是教会的永久成员,教会的名誉对他们至关重要。他询问他们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并让他们自行决定应该怎么做。他们选出了几位代表,去拜访那些离弃信仰的基督徒,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危险,并请他们决定要站在哪一方:站在基督的一方,还是站在异教的一方。他们派出代表,带着祈祷,听取报告后心存感恩。几天后,大部分离弃的信徒被重新接纳回教会。
有一个案例更为复杂。在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教会中的一位显赫成员赶走了他儿子的妻子,并为他安排了与一位迫害者社会中领袖的女儿结婚。这件事发生在传教士到达该地区之前已有两年多。两年间,这个过错一直没有被提起。这个犯错者和他的儿子名义上仍是基督徒。一旦传教士发现了此事,他召集了教会成员。再次,他向基督徒强调宽恕这种过错所带来的严重且明显的危险。然后,他让他们思考应该如何处理。过了一段时间,教理教师和教会中的几位成员来到他面前,告诉他,教会一致认为应该公开开除这两位犯错者。对此他回答说,本地教会没有权力开除任何成员,他们能做的只是将决议提交给主教,请求他采取行动。他表示愿意以教会的名义写信给主教。于是他这样做了。
但与此同时,他遇到了那位犯错者,并告诉他教会正在采取的措施。那人来见他,显得十分不安。“为什么,”他说,“你不能像你们的前任一样行动?以前,如果有人做错了,神父写信给主教,主教再写信给教会,信在教堂里宣读,犯错的人避开,然后就再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为什么要让所有的基督徒都卷入这些事情?”传教士回答说,公开的、众所周知的罪行不仅仅是神父和主教的事情,而是整个教会的事情,教会理应以集体的身份来处理这样的情况。“那我该怎么办?”那人问。“我无法忍受。”传教士回答说,他不清楚该怎么办,但他认为,如果那人真心悔改,公开在教堂里认罪,并在城里张贴自己的忏悔,使教会的名誉得以清白,那么基督徒们可能会满意,他也可以作为悔改者继续留在教会里,直到上帝的手为他指引恢复的道路。于是,那人离开了。
之后,传教士遇到了教理教师,并告诉他所说的话,询问他是否认为基督徒们会满意这样的忏悔行为。“他们怎么想并不重要,”教理教师回答道,“这种事情自世界以来从未发生过。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不会那样做。”然而,他做了。被主教开除是一回事,但被邻居开除则是另一回事。整个教会陷入了骚动。许多基督徒与犯错者有亲戚关系,他们对此事十分重视。教会里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日日夜夜都为此祈祷。那人站起来,在教堂里宣读了简明而明确的认罪词。在认罪词中,他承认自己犯了这样的过错,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上帝和教会的律法,他坚信在基督和祂的教会里能找到救赎,从此他会尽力使自己的生活符合上帝的律法。随后,他和教会的几位领袖一起,把这份认罪词张贴在城门的四个门口。
很快,传教士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将教会视为一个整体。当问题出现时,他只有一个回答:“告诉教会。”有一天,一位男子来找他,诉说了长长的迫害故事。他说,自己的一块地标被一位异教邻居搬走了,而那邻居不仅偷了他的东西,还指控他自己犯了他自己曾犯的错。受害的基督徒请求帮助以对抗他的敌人。他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告诉教会。”最后,他这样做了。一个星期天的主日礼拜后,他站起来说:“我有事要向教会汇报。”所有人耐心地听他讲完了整个故事。然后,一位年长的农民站起来问道:“你的对手把此事告到法庭了吗?”“没有,但他威胁要这么做。” “那么我提议我们先暂时搁置此事,直到他实施他的威胁。”没有再说其他话。几周后,这位男子又来到传教士面前,说他的敌人已将案件告上了法庭,并请求帮助。又是一位年长者站起来:“我认为我们最好再也不讨论这个问题。”再次,所有人都默默接受了这个判决。在这片寂静中,整个教会已悄悄地判定了那位兄弟的错误。他们认为他错了。一个本可能让外国人感到困惑且让他做出严重错误的疑问,就这样被解决了。教会里没有人敢告诉传教士那个人错了,也没有人敢建议他不为别人提供帮助。但没有人愿意自己为邪恶辩护;没有人需要打破那沉默的谴责。大家都知道案件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些细节没有人会敢私下说出来。那位年老、受人尊敬的领袖,尽管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愚钝,尽管他可能是个平凡的人,却在教会的议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履行了一个职责,这个职责会让最受过良好教育、最聪明的教师也感到为难。
很快,教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一个又一个的主日,教会会众坐下来讨论教会的秩序问题,或是彼此传授信仰。传教士大多数时候都不能亲自到场;而当他可能在场时,他反而认为让会众自己解决问题更为明智,于是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讨论问题和困难,等他们做出决定后再向他报告,或者如果有需要再向他求教。他不害怕他们会犯严重错误或在背后做出仓促的决定。越是他从他们中间退后,越是他们在有需要时转向他,越是他们寻求他的建议,越是他们告诉他他们的计划,越是他们帮他避免了困难。有一天,在他从一个偏远村庄回来时,迎接他的教理教师问了一个熟悉的问题:“您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吗?”“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我们领养了一个婴儿。”一群基督徒的孩子在田野里玩耍时听到了哭声。他们四下寻找,终于发现一个箱子,箱子上轻轻地覆盖着泥土,哭声正是从那里传来。他们把箱子打开,发现了一名婴儿。他们把它带回了家。那位父亲十分贫困,完全无力养活这个孩子。所以,第二个主日,他去教堂讲述了这个故事。于是,基督徒们决定把这个婴儿交给其中一位成员照顾,并每周支付一些生活费。婴儿被取了一个名字,英文意思是“获得爱的那个人”。当传教士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感到很高兴。如果他没有教会人们“告诉教会”,婴儿可能会被丢在他家门口,他也许会被迫开始建立一个昂贵的“弃婴之家”。但幸运的是,教会已经学会了管理自己的事务。
有时候,他也会建议给予慈善帮助。有一天,教理教师告诉他,一个贫穷女人的丈夫去世了,她的家人正为安葬事宜困难重重。“让某某人把这个情况带到教会面前。”会议后,传教士问教理教师教会做了些什么。教会捐了多少钱。“够吗?”“差不多。”然后,传教士作为教会的一员,也可以捐助。他不在教会之外,他可以和教会一起行动,但不能代替教会,或在没有教会的情况下行动。
所有这些听起来可能很微不足道。但它确实使得教理教师看到了本地教会的希望,远比他所受的所有教义教育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不到三个月,他就学到了这一课。这里记载的所有事情发生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和许多人在那段时间结束之前,就已经深刻理解了这个局势的真相。一天,教理教师走进传教士的屋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先生,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知道。”传教士回答,“我想我知道,但我想知道您认为我在做什么。”教理教师回答:“先生,如果您继续这样下去,您将建立一个本地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