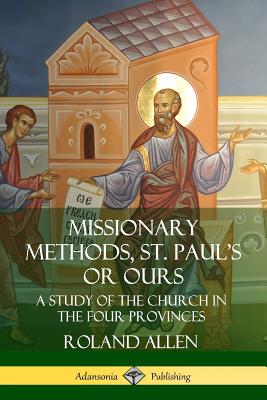本文译自书籍 “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A STUDY OF THE CHURCH IN THE FOUR PROVINCES, BY ROLAND ALLEN(FORMERLY MISSIONARY IN NORTH CHINA)
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并没有以一位孤独的先知身份开始他的传教之旅,也不是传扬一种孤立的个人主义宗教。他是作为教会的使者被差遣出去,把人们带入与这个身体的团契中。他的皈依者并不仅仅因为住在同一地方、信仰相同的教义,认为彼此形成一个互助社群而团结在一起。他们是因为受洗而彼此联合的。每个人都因一个圣灵的团契而与任何其他基督徒紧密相连。每个人都通过共同的仪式、参加相同的圣礼,与所有人联合在一起。每个人都因共同的危险和共同的希望而与所有人联合在一起。
同样地,他们所属于的教会并非独立和分散的团体。它们既不独立于作为共同创立者的使徒,也不独立于彼此。我们已经看到,在他的宣教过程中,保罗的目标是将整个省份带入福音之中。他的计划是考虑到省份,而非城市。在他心中,省份才是单位。因此,当他的教会成立时,他明确承认了省内教会的合一性。他常常提到马其顿、亚该亚、加拉太、叙利亚、基利基亚、亚洲等省份的教会,视它们为一个整体。为了向耶路撒冷贫困的圣徒募捐,马其顿、亚该亚和加拉太的教会被视为独立的群体,每个群体选出代表来处理捐款事务。在每个省份中,教会可能通过某种外部的组织和管理形式紧密相连。
然而,这种合一并不只是方便地将独立的社团归为一类。正如联合个人基督徒的纽带把教会中的所有教会团结在一起。这些教会不仅仅是为了相互援助和便利而在面对共同危险时联合起来的基督徒群体。它们都是某个身体的成员,而这个身体早在它们被带入其中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们不能把自己当作只对自己负责的存在。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批评他们允许妇女在教会里发言,他写道:“神的话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单临到你们的吗?” 或者在定下妇女在教会中应戴头巾的规则时,他总结道:“若有人想要争论,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教会也是如此。”对他来说,教会是先于教会存在的。教会并非由教会组成,而是教会创立了教会。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在建立教会时选择了希腊和罗马文明的中心,而这些教会通过重要的商贸路线相互联系。因此,它们常常有频繁的沟通。访客容易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先知们很快就开始往返于各地,传道讲解信仰。这种频繁沟通的证据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不仅仅是保罗自己的皈依者,耶路撒冷的使者们也不断地从一个教会流动到另一个教会。看起来这是一种定期的书信推荐系统,任何被认为是受洗之人都会受到接待和款待。因此,这些教会实际上是通过许多个人利益的纽带紧密相连的。
但它们并不仅仅是通过个人利益的纽带联合起来的。正如个别的皈依者联合起来,城市的教会联合起来一样,省份的教会也联合在一起——它们的联合不仅仅是出于信仰的共同性,还是真正的属灵团契。它们都是一个身体的成员。这个身体是一个有形的教会,容易受到明显敌人的攻击。它不仅仅通过便利、共同的信仰和圣礼联合在一起,还通过共同服从一个共同的创始人而紧密相连。各省份教会之间的联合不仅体现在常常相互交流,还体现在它们共同承认使徒的权威——作为基督给它们的使者。它们都是他的羊群;只要它们是他的羊群,它们就被认为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哥林多的教会背离了使徒,马其顿和亚洲的教会也许就不再承认它作为神的教会成员。
正是在这种原则下,我们才能理解保罗为维护他在哥林多教会地位所表现出的焦虑。如果教会是否承认他对教会的状况没有任何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假设他是出于个人的考虑,这也是通常的假设。然而,这不足以解释使徒的行为。保罗远比关心自己的个人地位更关心福音的进展。当然,如果没有其他解释他恳求皈依者不要弃绝他,那么我们只能接受将这些恳求归因于伤感情的解释。但如果拒绝使徒会导致承认他权威的教会与拒绝承认他权威的教会之间的分裂,那么整个问题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我们就看到,使徒面对的是一场威胁到教会生命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一点,他诉诸于任何可能帮助他保持皈依者走正道的情感和情绪。这才是使徒应有的行为。但是,如果拒绝他的权威并不会伤害教会,使教会仍然与基督的一个教会保持一致,那么他就只是在为自己的职位而斗争了。
此外,四个省的教会并不独立于那些保罗未曾创立的教会。犹太地的“神的教会”在这些教会之前就在基督里。保罗是被叙利亚的教会差遣出去的。四个省的教会与它们是联合的。使人成为基督成员的纽带使他们也成为教会的成员;而教会并非只是所在城市的教会。四个省的教会之间的联合就如同各地教会之间的联合一样。外在的这种合一由使徒团体来表现。一个个人皈依者是否应被认定为教会成员并被接纳参加团契,由他所居住的城市或城镇的教会来决定。如果那里的教会接纳他为团契成员,他就被接纳了。一个城市或城镇的教会是否应被承认为该省的教会成员,由该省的其他教会决定。如果其他教会承认它,它就被承认;如果他们不承认它,它就不被承认。在亚洲,我们熟悉一些重要的城市教会,保罗本人并不认识它们。以弗所的教会承认它们:使徒也承认它们。类似的进展在加拉太、马其顿和亚该亚也在进行,保罗不在时也遵循同样的做法。如果一个省的教会的正统性存在疑问,那么这个问题由使徒会议来决定;而创立该省教会的使徒则是该省在会议中的代表。
保罗从一开始就关注合一。在他看来,教会的合一并不是要创造的东西,而是已经存在并需要维持的东西。教会不是独立的统一体:它们是已经存在的合一的延伸。在同一地方,不可能有两个教会都持有基督为头,却不相互交往。不同地方的两个教会,也不可能都持有基督为头,却不在团契中。一个基督徒如果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必然与所有其他基督身体的成员联合。如果一个肢体与基督为头联合了,他就必然与所有其他肢体联合。
在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个神和一切之父里有属灵的合一。在外在上,这种合一体现在共同承认使徒权威、共同参与宗教仪式和共享社会交往中。没有属灵合一而在外在分离的事物。属灵合一就是合一,它意味着合一,并以合一的方式表现出来。外在的对立是属灵合一不存在的明确标志。属灵合一在其完美与充实的程度上,必然以共同、团结、和谐的表达方式展现,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否则,灵魂可能属于上帝,而身体却属于魔鬼。
这种合一必须得以维持。保罗写信给教会时常提到合一,但他从未把它看作是他们所创造的东西。他总是把它看作是神圣的事实,破坏它就是罪。合一是可以破裂的。属灵的骄傲可能表现为自我主张;自我主张可能导致公开的分裂。身体可能被撕裂。但那是对圣灵的罪:它是要摧毁主的殿。分裂的行为表现和表达了一个分裂的、不慈悲的心灵。只要爱心达到完美的工作,意见的分歧就不可能导致分裂。外在的撕裂意味着内在的撕裂。基督徒的分裂意味着基督的分裂。
合一是可以破裂的。威胁它的危险是极其深刻和严重的。教会最初在耶路撒冷是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群体,他们小心维护自己的犹太传统,遵守祖宗的习惯。而四个省的教会几乎完全由不懂得这些传统的外邦人组成。因此,如果马其顿或亚该亚的一个基督徒上耶路撒冷,他一定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陌生的氛围中,周围的社区与他习惯的完全不同。那里实行割礼,守安息日,避开不洁的食物,律法是日常生活的实际规则。那里的严格和保守必定使他感到压抑和沮丧。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看起来几乎与犹太教没有区别,许多基督徒避开外邦人,或者只把他们当作一种类犹太教徒来容忍。在教会的集会上,祷告按犹太式模式进行,用犹太语言表达犹太思想,他并不熟悉。唯一的联系点就是共同的对耶稣的敬拜,共同承认相同使徒的权威,以及共同遵守洗礼和圣餐的仪式。另一方面,当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来到哥林多时,震惊更为严重。哥林多的教会的基督徒会发现,这个社会严肃、笨拙、严苛、形式主义,甚至令人压抑。犹太教徒在哥林多一定会认为,那里的教会纵容无法无天的行为。没有受割礼的基督徒参加他们异教徒朋友在神殿中的宴会。甚至在每一天,礼仪法的每一条都似乎没有受到谴责。即使在教会集会上,讲道和祷告也建立在一种几乎无法称之为基督教的思维体系上,且行为举止自由无拘。他一定会欢迎来自自己城市的派别领导人,他们认为与这种人群打交道时,妥协毫无意义,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全教会内强制执行整个律法的遵守。忽视任何一条就等于承认分裂基督教道德的缝隙。要得救,必须遵守律法。
即使在他们自己之间,希腊人也并未达成一致。在教义和实践上有不同的学派。
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关于洁净和不洁的食物在旧约中的规定,或关于偶像实际上是超人类灵魂借以与人类交往并使人类能够通过祈祷和祭品接近这些灵魂的工具,具有一定重要性;或者他们认为,忽视圣日确实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另一些人则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正是从这种宗教中,基督才来解救人类,福音并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行为或事实。有些人甚至说,连基督的复活也应当被属灵的人看作是一个属灵的事实,而不是物质的事实;如果被理解为一个属灵的事实,基督徒通过信心属灵地分享了这一复活,那么就不必相信任何实际的身体复活;即使基督的身体复活,也不必认为其他人的身体也会复活,因为基督徒因信仰基督,已经在属灵上复活。
因此,不仅仅是在各省教会中有分裂的危险,甚至更大的危险是犹太地的教会可能完全否定并将四个省的教会逐出教会。要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合一,是一项不小的任务。那么,圣保罗是如何克服这一困难的呢?
合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保持。耶路撒冷的教会可以被视为原始教会——由基督的使徒所建立和组织的基督之体——而四个省的皈依者可以视为加入了那个教会。在这种情况下,新成员必须愿意接受他们加入的社会的规则和传统,任何反叛这些规则和传统的行为都必须视为分裂行为。耶路撒冷的当局必须被视为最终的裁判所,任何违抗行为都必须在这里受审。必须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这就是罗马式的体制,这种体制在现代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即使那些拒绝教皇主权的人,在建立传教事业时,也忍不住在原则上采用它。
另一方面,省份中新建立的教会可以同样被视为第一个教会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尚未完成的整体,必须逐步成长为它的完全体。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入的成员会立即被承认为是一个圣灵充盈的身体的成员,享有与老成员同样的圣灵启示。老成员的规则和传统不能被视为最终的和普遍的义务。第一个教会有其适应自己思维习惯、满足自身需要的传统。最后一个教会也可能有其适应自己思维习惯的传统,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第一个教会仅仅因为是最早的,就没有权利将其法律和习惯强加给最后一个教会。换句话说,合一并不在于外在地遵守最早成员的实践,而在于融入这个身体。因此,最早的教会主张支配最后一个教会的权利,与最后一个教会宣称其独立性一样,都是一种分裂行为。
正是第二种政策,圣保罗所采纳的。他拒绝将犹太地教会的法律和习惯移植到四个省。他拒绝建立一个中央管理机构,从那里教会可以收到关于地方事务的指示。他拒绝设立普遍适用的正统标准,这些标准应当适用于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情况、所有的地方。他拒绝允许特定先例的普遍适用。
- 他拒绝将犹太地教会的法律和习惯移植到四个省。为此,他每天都面临生命的危险;为此,他忍受了污蔑、迫害、诽谤;为此,他冒着一切风险。他自己遵守律法,但这对他毫无益处。他被最残酷、最恶毒的敌人追捕,从一个省份追到另一个省份,从一座城市追到另一座城市。他的工作被阻碍,他的皈依者被误导,他的劳动被加重,他的体力被消耗殆尽。然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道路,基督教在当时已知的世界的建立便是他的回报。
- 他拒绝建立任何中央行政权威,使全教会从中获得地方事务的指示。曾经有一次,他支持向耶路撒冷大会上诉,解决另一个省份中出现的问题。那个省的教会并非由他创立,弟兄们认为上诉是合适的。但从四个省没有类似的上诉。当相同或类似的困难在这些省份中出现时,他将这些问题视为每个省、如果不是每个教会,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他提供了建议,并信任教会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当来自耶路撒冷的使者攻击他时,他前往耶路撒冷,不是为了参加一个可能推翻各省的大会,而是为了维护各省的正统性,捍卫它们的自由。
- 他拒绝建立任何先验的正统性测试。我们这些急于寻找正统性测试的人,总是希望在事先明确规定教会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什么是必须坚持的,而不是被视为离开天主教会的行为,在使徒行传的记录中寻求这种测试。我们未曾找到它。我们知道圣保罗明确教授了什么。我们看到他如何传承传统和圣经,如何建立圣职的秩序,如何坚持圣礼的适当管理。但从否定的角度看,什么都没有明确规定。很奇怪,我们竟然很难找到任何明确的指导。有一个点,教会不能再越过,否则将被排除;就像一个个人如果越过某个道德行为的界限,也不能不被逐出一样。但正如在哥林多的情况一样,律法并没有事先规定。就像没有定义哪些罪行会导致个别皈依者被逐出一样,关于一个教会的不正常行为达到什么程度会导致它被视为叛教,并需要排除,也没有事先规定。
圣保罗从未告诉我们,如果某些事情发生了,尽管实际上并未发生,结果会怎样。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能力拒绝定义或预判任何异端或分裂。他预见到会有异端,甚至必然会有异端,但他拒绝在罪行实际发生之前就做出判断。
- 他拒绝允许先例的普遍应用。当一个问题已经出现,并作出了判断时,他并没有将这一判断作为具有普遍权威的原则来应用。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是针对叙利亚和基利基亚的教会。圣保罗将它们带到加拉太,但他没有将它们推广到更远的地方。他没有在马其顿或亚该亚强制执行这些决议。先例并非普遍适用。哥林多或帖撒罗尼迦的情况与叙利亚的安提阿,甚至与加拉太的情况不同。在叙利亚是至关重要和自然的,在亚该亚则可能显得人为。它不会成为哥林多人或帖撒罗尼迦人的先例,而只是一个完全武断的裁决。问题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而是会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以不同的形式重现。它们必须被重新阐述;而答案必须由当地的教会重新阐述和修正。没有什么比以先例判断代替以信念判断更危险了,而这恰恰是最容易的事情。寻求耶路撒冷、特伦特、兰贝思或威斯敏斯特的答案很容易,但这是灾难性的。它给人一种统一的假象,破坏了真正的合一。定义和先例造成的分裂,远超过它们所治愈的分裂。如果定义和先例在本土是危险的必要条件,那么它们被移植到外国时,就成了危险的多余品。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担负自己的重担”是一个真理,那么同样的真理也适用于每个时代都必须产生自己的定义,每个教会都必须产生自己的先例。
圣保罗的合一观念是如此属灵,以至于它不可能仅仅通过保持统一的实践来实现。它是如此属灵,以至于无法强制执行。它是如此属灵,以至于要求在外在的统一中表现出来。唯一重要的是属灵的合一;外在的合一,如果不表现内在的合一,便是空壳。但内在的合一是唯一重要的,因为内在的合一如果没有表现为外在的合一,便是否定合一。
因此,他非常重视合一。
(1) 他教导合一。他通过理所当然的方式教导合一。他教导人们意识到合一是他们基督徒经历的一部分。他教导他的皈依者将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视为兄弟。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他教导他们相互之间有责任。他通过不断提醒他们彼此共同的困难和苦难,在信中提到其他教会的苦难,并将它们与自己的苦难进行比较。他教导他们彼此款待。无论何时,以各种方式,他始终将教会合一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
(2) 他充分利用自己作为犹太人和希腊人之间的中介的身份。他是一个受过希腊教育的法利赛人,完全理解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当他在耶路撒冷时,他严格遵守律法,同时他也极力主张希腊人的自由。他受到所有教会领袖的信任,并不断利用这种影响力。在这十年中,他三次上耶路撒冷。第一次是通过加拉太后,他返回安提阿,再从那里上耶路撒冷参加会议。第二次,他认为自己在耶路撒冷的出现至关重要,因此拒绝了紧急请求,要求他留在以弗所——一个他早就打算传教的中心。第三次,他坚持不顾一再的警告,仍然前往耶路撒冷。他的这种关心的唯一合理解释是,他知道只有通过个人的干预,他才能将犹太地和四个省的教会维系在一起;只有通过个人的干预,他才能抵制那些希望将犹太律法强加给外邦人的党派,从而避免分裂或毁掉他的工作。
(3) 他通过发起和鼓励互助行为来维护合一。为耶路撒冷犹太圣徒募捐,既是合一的证明,也是合一的保证。圣保罗急切地推动这项募捐,广泛认为这是因为他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并且确信这项福音的团契标志将在与耶路撒冷的犹太化党派的斗争中为他提供巨大的力量。没有什么比一个单一的慈善行为更有力地证明正统立场。当我们在外在协议背后看到的真正合一时,它就是共同参与基督的精神,爱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一个标志促使人们抑制自己的怨言,承认他人的正确,而不仅仅是许多正统实践的声明。而募捐的影响在于,耶路撒冷教会拒绝支持犹太化传教士一方。
(4) 他鼓励不同教会之间的不断沟通。他鼓励各教会共同为共同的目标行动。为耶路撒冷贫苦圣徒的募捐,不是分开在加拉太、马其顿、亚该亚和亚细亚各地的独立募捐,而是这些教会共同进行的募捐。如果它帮助将耶路撒冷的教会与四个省的教会联系在一起,它也帮助将省份之间的教会互相联系在一起。它们都派代表和使徒一起前往耶路撒冷。当他上耶路撒冷时,他是带着一大队人马一起去的。在他和他同行的人中,有一位希腊人,这直接导致了骚乱。要反驳歪曲的言论,没有什么比许多证人更有价值。有些人可能会看到事情的最糟一面,但在很多人中,总会有人看到最好的方面;而多数人的证词会趋向正确的判断。因此,国外教会和本地教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便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互相帮助彼此理解教会的合一。
圣保罗通过这些方式教导他的皈依者意识到合一的事实。
今天,我们的宣教工作维系合一的方式与过去大不相同。我们经历了长时间且非常痛苦的分裂,所有的宣教工作都是在这种分裂的恐惧中进行的。我们对待皈依者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恐惧的结果,而我们的方式也是它的产物。我们在国外没有建立与四个省教会相当的体系。我们只是将我们在本土熟悉的组织移植到国外。我们通过派遣大量欧洲官员来维持它,认为迟早我们会把本地人培养到一定的水平,以至于最终如果他们成为教会的主导力量,变化不过是人员的更替。这个系统将照旧运行,本地人将仅仅做与我们现在做的相同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主要把合一视为组织问题。
当我们在国外建立一个宣教工作时,我们通常会让一位欧洲人担任一个庞大教区的主教,并且这个教区的管理基本上和本土的教区一样。他的下属是一些白人神父,他们负责的地区习惯上被称为教区,他们以和本土教区神父类似的方式管理这些地区。外部有一些不同之处:他们的信徒比较分散,因此,负责的神父尽可能多地在各地巡回,并为那些不常上教堂的信徒举行更多的布道服务。他们下面有神父、执事或教理导师,负责在较大的或较小的传教站点服务,他们与本土的教区助手、普通读经员的关系类似。他们的礼拜形式和本土教会的几乎完全相同。他们使用相同的《祷告书》和礼仪。
如果一个旅行者从印度或中国的基督徒群体回来,他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他很高兴发现自己在一个教堂里敬拜,虽然语言陌生,信徒肤色不同,但在其他方面他感到完全在家。他发现同样的装饰、同样的仪式、同样的祷告书和同样的赞美诗。如果一个中国或印度的皈依者来到英格兰,他当然会发现英格兰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基督教国家,大多数人并没有遵守他被教导要遵守的许多规则;但是在教会的圈子内,他发现与他在自己家中所熟悉的一切完全一样。所有宗教的外在形式几乎都统一。
当然,也有分裂,但这些分裂是我们自己的分裂被移植到外国的结果。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党派,并且允许国内外有党派的区分;但国内外教会之间并没有分裂。当然,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分裂带到国外,如高派与低派、礼仪派与反礼仪派——但我们不承认东西方在方式上的差异。我们无法找到与耶路撒冷教会和哥林多、以弗所教会之间的分歧相当的例子。要找到与我们现代宣教工作相似的例子,我们需要想象马其顿或亚该亚的教会是一个犹太主义的教会,分成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希腊派。事实上,我们必须想象圣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几乎都是犹太化的人。
没有来自欧洲或美国的使者回来指责某个本地教会违反了律法和习俗。没有主教急于回到家乡,要求为他所创立的教会争取精神自由,并主张它有权忽视某个礼仪。没有人敢声称一个教会与另一个教会平等,作为属灵身体的平等成员。伦敦的一个会议决定了一个规则,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其应用到中国和非洲;也没有人敢说中国人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的决定可能得不到英国人的认同,但这显然不是与他们断绝交往的充分理由。
如果改变几个名称,几乎可以将同样的描述适用于其他基督教团体的宣教工作。它们也将自己的组织和形式带到国外,它们也在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犹太化。
因此,我们所维持的合一,实际上是一种风俗的统一。它本质上是法律性的习惯。当问题出现时,由宣教士来解决;而宣教士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与西方做法的一致。如果找到了先例,那先例就解决了问题。如果找到了适用的西方教会的规则,那就必须遵循。如果没有适用的法律或先例,那么就会建立一个看起来最符合西方教会精神和历史的规则。
通过这种方式,必须承认我们在维持某种合一上取得了一定成功。分裂和异端几乎在我们的宣教工作中没有出现。但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如果没有异端,就没有先知的热情。如果没有分裂,就没有自我实现。如果没有异端领袖,就没有教父。如果没有分裂者,就没有使徒。如果没有异端,就没有本地神学。如果没有分裂,就没有宗教生活的强烈爆发。如果没有与我们创立的教会之间的分裂危险,就没有教会宗教生活的伟大进展。新教会在东方的建立应该给我们带来与新希腊教会建立时一样的收益。但只要我们继续认为东方人民的归信只是使他们成为我们所属教会的信徒,我们怎么能期待这种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