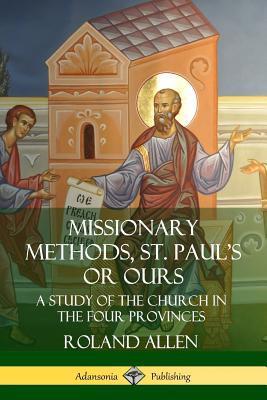本文译自书籍 “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A STUDY OF THE CHURCH IN THE FOUR PROVINCES, BY ROLAND ALLEN(FORMERLY MISSIONARY IN NORTH CHINA)
随着长老的任命,教会得以完成,变得完全装备。它们很快熟悉了所有的事工命令,无论是永久性的还是属灵的。它们不再完全依赖圣保罗。如果他离开或去世,教会依然存在,并且在人数和恩典上都得到了增长:它们成为了属灵的中心,逐渐驱散了周围异教的黑暗。在加拉太,教会在信仰上得到了加强,每天都在增长。从帖撒罗尼迦,“主的话语传播”到了马其顿和亚该亚。从以弗所,福音传播到所有邻近的地区,许多教会纷纷兴起,教会的成员们甚至未曾见过圣保罗的面;他自己甚至可以写信给罗马人,称他在那些地区“再无可容身之地。”
它们不再依赖使徒,但也没有脱离他。当有需要时,他毫不犹豫地宣称对他所创立的教会拥有权威,并且声明他是从主那里直接得到这一权威的。“即使我在我们所拥有的权威上稍微夸耀一下——这是主赐给我们的,用来建立你们,而不是摧毁你们——我也不至于羞愧。”当他认为有必要时,他可以用“我们没有这样的惯例”来制止反对者。他制定了普遍的原则:“主如何分配给每个人,神如何呼召每个人,就让他照着行。”并补充道,“在所有的教会中要这样命令。”
他为公共敬拜制定了一些指示,并总结道,“其余的我到时会处理。”当人们抗拒他的权威时,他提议设立一个法院,在那里每个证词都应由“两三个人作证”来确立,并威胁说:“如果我再来,我不会手软。”
关于这些使徒权威的声明,有必要注意,它们都出现在写给一个教会的书信中,并且大多数是因应那些不合理和无序之人的严重行为。它们显然并不代表圣保罗对他所有教会的普遍态度。它们甚至并不代表圣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态度。在这些威胁的书信中,他明确否认他有“主宰他们信仰”的权力。尽管它们确实证明使徒意识到他拥有在必要时可以依赖的权力,但它们也证明了他是如何非常节制地使用这一权力的。他必须处理一些可能激怒教会的最紧迫和最困难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我们自然会认为,最容易且最有效地解决的办法是通过依赖权威。然而,他几乎从未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而是宁愿通过疑虑和争议来避免强制服从规则。我们应该仔细审视这些案例,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使徒方法的重要洞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成功的秘诀。
他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个人纯洁、合适的行为以及吃祭偶像的食物。
- 淫乱
性不道德在外邦世界的普遍性,是犹太党派在教会中最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们合理地认为,如果外邦人被接纳为教会成员,而不强迫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教会的道德标准很快就会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而当他们未能强制要求外邦基督徒遵守摩西全法时,他们成功地使这类罪行成为耶路撒冷会议的四项重要法令之一。
这一事件证明了他们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宣讲刚刚结束,他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信时,教会的情况依然在他的关注中。然而,淫乱和通奸是他劝诫的首要问题之一。 他离开哥林多教会不过两年半,写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时,尽管教会曾接受过亚波罗的教导,并且以丰富的属灵恩赐而闻名,但淫乱仍然是普遍的罪行。
那么,圣保罗是如何处理这一严重问题的呢?在他的信中,没有一字提到律法。他没有暗示耶路撒冷会议就此问题颁布了任何法令。他也没有提出需要一套规则或罚则表。他没有威胁犯错者惩罚。他恳求并劝勉那些已经接受圣灵的人,顺服圣灵的引导——认识到圣灵赐给他们,是为了使他们在身心上成为圣洁,而污秽必然意味着拒绝圣灵,并招致神的愤怒。
例如,在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书信中,他是这样论述的:他提醒读者他当初在他们中间的亲自教导。他提醒他们,神对他们的旨意是成圣。他建议基督徒的行为应该与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有所区别。他警告他们,主是这些恶行的报应者。他重申神呼召他们从外邦世界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成圣。最后,他警告他们,如果拒绝他的教导,就是拒绝圣灵。
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语言同样相似。有人认为在某一节中,他似乎建议对犯淫乱的信徒实行开除,因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要与那被称为弟兄的淫乱者交往。”但这显然并不是指正式的开除教籍,因为它不仅仅包括淫乱者,还包括贪婪者、谩骂者、勒索者以及醉酒者和拜偶像者;同样的话语适用于与外邦人和基督徒的交往。这是对好基督徒的劝告,鼓励他们通过避免与其交往来悄悄纠正弟兄们的错误。
这更应当与他在第二封帖撒罗尼迦书中的劝勉相比较,“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要远离一切行为不端、不照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传统行的弟兄。”而不是与“除掉旧酵”和“交给撒旦”相对比。前者是劝告“把人放到科文垂”(即孤立),后者则是“开除他。”
排除这一点后,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其他地方的语言,和他在帖撒罗尼迦书信中的语言性质完全相同。他认为,淫乱是对身体真正用途的亵渎,是对复活荣耀盼望的违背,是亵渎基督的肢体,身体不是基督徒可以随意使用的,而是圣灵的殿。
确实非常奇怪,圣保罗甚至没有提到耶路撒冷会议已经定罪这一罪行。更奇怪的是,当他谈到淫乱时,特别是与一宗明显的乱伦案件相关时,他甚至没有暗示这违反了十诫。显然,圣保罗并没有依赖律法,他并没有寻求从任何命令或权威行使中找寻道德生活的源泉。他的福音不是律法的福音,而是圣灵的福音。
在这一点上,他遵循了基督的榜样。人们经常指出,耶稣的方法是教导原则,让门徒自己去应用这些原则——只是指出他们应当走的方向,而不具体规定他们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圣保罗在跟随基督的同时,罗马的克莱门特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也遵循了这一规则。
《哥林多书信》的一大特点是,作者从未忘记他的职责是指引正确的行动方向,而不是对教会下达命令。一次又一次,他表达了对教会的坚定信念,认为教会知道神的旨意,并会顺服圣灵的引导。
但有可能有人说,哥林多的教会具有如此独立的精神,并且对自己的能力有如此强烈的自觉,以至于它不可能容忍任何更专制的治理方式。哥林多人显然不愿意仅凭使徒保罗的权威来接受指导。当然,这种说法是对的。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如果他们在皈依时,便被接纳进入一个宗教社会,且其最显著的要求是遵守权威所设定的法律,他们就会明白,只有服从权威才能成为基督徒。服从和顺从将成为最主要的教义。每一个皈依者的首要责任将是遵守规则。如果使徒保罗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一教会的面貌——即一个每个进入者都必须遵守规则的社会——那么哥林多人和所有其他的皈依者就永远不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正是保罗不相信的,因此他无法教授这种教义。如果他一开始就采取这种方式,那么哥林多教会中出现的问题就不可能以它们的方式呈现出来,保罗也不可能以他所采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可能会出现对权威的反叛,但那将是对整个教会体系的反叛,保罗必须通过权威来压制,否则教会就会失去哥林多。
- 诉讼问题:一些哥林多的基督徒显然在异教法庭上起诉他们的弟兄。这显然是一种可能会给基督教名声带来不良影响的行为。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是通过法令禁止这种行为,并威胁未来的违法者。可是保罗并没有这样做。他与全体信徒辩论,并将他的观点呈现出来,然后让问题留给他们自己。他向他们展示了他们行为与作为基督徒的身份之间的显著不一致。他说,作为世人和天使的审判者,他们将弟兄们带到异教法官面前是多么不合适。他指出,如果在教会中找不到一个人来解决争议,这就反映出教会的智慧和道德标准低下。他劝告他们宁愿忍受损失,也不要把教会的丑闻公之于众;而且伤害和欺骗弟兄们,就会使自己像异教徒一样。他警告他们,那些这样做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这与为教会立法完全不同。立法者的任务不是与人辩论,也不是劝告受害者默默承受,而是通过制定法令。保罗没有立法,也没有敦促他们立法;他是在向他们内心的圣灵呼吁。他没有暗示如果他们拒绝听从他的劝告,他会采取任何行动——某些人肯定会拒绝听从他的辩论。对于他们,保罗没有威胁采取任何行动,而是警告罪人将被排除在上帝的国度之外。
- 食物问题:在耶路撒冷会议中已决定外邦基督徒应避免食用献给偶像的食物。而在哥林多,有些人不仅食用了献给偶像的食物,还参加了偶像庙里的宴会,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罪行,通常还伴随着其他罪行。面对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认为应当引用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并用“禁止”来关闭所有的异议。但保罗却不这样做,他不仅没有自己立法,甚至没有提到任何相关的法律。如果没有其他来源的背景知识,哥林多的信徒根本无法从保罗的教导中猜到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他不仅没有引用它,甚至也没有坚持它。在哥林多,是否可以吃献给偶像的食物成为了一个争议问题。保罗没有作出决断。他显然不赞同这种做法:“我不愿你们与鬼有交通。”但他说,“我说话是对明理的人,你们要判断我说的。”他呼吁他们发扬基督徒的博爱精神。他说,有些人知道偶像什么也不是,他们可以吃献给偶像的食物而不认为偶像是神。他们没有意识到偶像的存在,并且觉得自己超越了这些虚幻的东西。但有些人依旧保持着以前的迷信。他们无法摆脱偶像确实是某种该敬畏的存在的观念。他们无法摆脱与偶像一同共享宴席所带来的不安,虽然他们羞于拒绝那些更大胆、较为开明的弟兄们所做的事,他们还是吃了,并且感到有罪,良心不安,觉得自己在基督面前犯了罪。因此,保罗向他们呼吁最崇高的基督徒美德。他把知识和博爱进行对比。他说,倘若依赖知识,执着于纯粹理智的自由,毫不顾忌地展示真理,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追求真理,这并不是基督徒的行为。他强调博爱应当先行,如果基于知识而做出的行为伤害并误导了软弱的弟兄们,这不仅不是值得称赞的,反而是罪恶的。伤害软弱弟兄的良心就是犯罪。
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现代的欧洲传教士会这样做。如果他的某些皈依者表现出一种趋向去磕头于孔子的石碑,理由是他们很清楚孔子只是一个人,做这个动作只是对他作为民族教师的美德表示尊重,他会写信让他们判断是否继续这样做,依据的是博爱的原则吗?还是会与其他欧洲传教士协商,可能完全不与当地基督徒商量,直接给教会制定一个规则?如果他是天主教徒,他会不会引用克莱门特十一世的法令,并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我们与本土皈依者的接触中,我们习惯于诉诸法律。我们试图执行一套与他们思想完全不符的法律;我们引用的先例对他们来说并不成立;我们引用的决定他们既不理解其历史背景,也不理解其理由。在没有让他们理解的情况下,我们仅凭命令来解决问题。
这种做法是不幸的,因为它让人未被说服,也没有教育意义,它只教会了人盲目服从的习惯。人们学会了期待法律的出现,学会了精确遵守详细的指示。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使得当最重要的是唤醒他们的良心时,他们无法做出回应。失去了精确指令的人会感到无助。当他们不再期望理解事物的缘由或运用自己的智慧时,他们会选择信任外国引导者的正式指示。最终的结果是,当传教士无法或不愿提供精确的指令时,他们对传教士的神圣劝告毫无兴趣。没有先例支持的建议显得软弱。任何不直接违背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容忍。诉诸原则的呼吁看起来模糊且难以理解。人们不习惯于思考这些问题并应用它们。如果传教士告诉他们某个行为与基督的心意不合,他们的话语往往被忽视。如果他告诉他们某个行为在某个会议上被禁止,他们会照做。但这是一条死亡的道路,而非生命的道路;这不是基督教,而是犹太教;这不是保罗式的教义,而是教皇式的教义。
保罗肯定不认为通过诉诸博爱,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他必定预见到了纷争和分裂。他必定故意选择了纷争、内心的煎熬、痛苦与失败,而不是下达一条法律。他看到了,通过许多的失败,皈依者比通过一条捷径走向安定更加有益。他认为,为福音的缘故,哪怕是一次自愿的自我放弃,也比一种表面的顺从法律要更重要。
通过这种拒绝对是否允许基督徒进入偶像庙的判定,保罗避免了一个我们在工作中常常遇到的重大困难。他使得皈依者可以继续在异教的工会或社团中工作。显然,四省的基督徒中,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是商业或工匠阶层,他们并没有因异教仪式的存在而放弃他们的工作。那些是奴隶的人无法避免参加异教仪式;而大多数自由人可能只有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做到避免。他们在场,但并不参与其中。特土良在《偶像崇拜》中指出,几乎每一项生意或工作都有可能让基督徒与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混为一谈;但四省的基督徒并未因此立刻切断与世俗的联系。基督徒并未因此断绝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或建立完全与世隔绝的基督教村庄。早期的基督徒和他们的孩子并没有因害怕受到偶像崇拜的影响而脱离世俗环境。他们没有把孩子从异教学校中拉出来,害怕他们被偶像崇拜误导。的确,在那些早期,也有些人选择放弃工作,宁愿贫困潦倒,也不愿继续在与偶像崇拜相关的行业中工作。而教会也很快开始为这些因坚持基督教教义而失去生计的人提供帮助。但大多数情况下,基督徒并不觉得必须放弃他们的工作,尽管他们所在的行业可能直接或间接与偶像崇拜有关。
在我们这里,确实存在一种倾向,鼓励这种与异教社会的分离,即与异教社会的物理分离。我们的皈依者常常停止生活在异教社会中。有时这是被迫的,因为他们被异教徒驱逐;但有时是自愿的。他们聚集在基督教村庄里,进入基督教作坊工作,不再在异教主人手下工作。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基督教学校,虽然异教徒的孩子也能入学,但那里严格的气氛和教学内容都是基督教的。
通过这种做法,我们得到了某些东西,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获得了免受诱惑的保护,皈依者享有基督教交往带来的特权和支持。监督他们变得更加容易。孩子们在没有面对异教学校和作坊的严峻考验下,成长为基督徒。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基督徒无法像他们生活在其中时那样渗透社会。他们与异教徒的生活不同,他们与社会的联系变得较弱,他们的宗教似乎与他们的民族无关。
当然,我知道这种批评在每个时代都曾针对基督徒。无论他们如何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都无法逃避这种批评。基督徒总是显得不同,显得可疑。但如果他们与外界隔离,单独聚集在小群体中,这种批评会更加尖锐,影响也更大,他们不能像真正与社会同在、共享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得失的基督徒那样,影响周围的人。基督徒和他们的宗教,似乎成了外国传教士的专责。他们被视为脱离了民族生活,他们的宗教似乎不属于他们的民族。
我知道,这样的批评早在每个时代就存在过。基督徒不论如何融入本国社会,总是会被认为是一个与众不同、让人怀疑的群体。可是,当他们选择脱离社会,聚集在一起时,这种批评显得尤为严厉,他们也无法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产生影响。此外,皈依者也会感到与外界隔离后,越来越依赖于外国传教士。他们开始更加模仿传教士,期待更多来自传教士的支持,逐渐采纳更多西方的生活方式。他们与周围的异教徒渐行渐远。传教士也因此受到影响。在不断地为基督教社群服务时,他自己与周围的异教徒也逐渐疏远。虽然照顾皈依者集体更为容易,但也更容易陷入过度管理的困境。传教士更多的是在“管理”信徒,而不是在“传教”。
我并不想过分强调或夸大这一点。但考虑到欧洲传教士通常过于喜欢行政管理,我想指出,将皈依者隔离成小团体,与本土生活隔绝,这一倾向并非没有其危险和缺点。相反,保罗更强调的是从偶像社会中精神上的分离,而非物理上的分离。
- 婚姻与离婚
或许有人会说,保罗在一件事上确实明确提出了法律。这可能是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关于婚姻的教导,这一章的语气看似充满权威。对此可以这样回应:首先,这一章是专门回应关于指导的请求;其次,保罗非常小心地区分了主的命令和他自己的意见;第三,关于婚姻的问题处理非常简略,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结论。例如,他似乎原则上认为,寡妇如果再婚,必须“只在主里”,即与基督徒结婚;但在讨论处女的婚姻时,他并没有坚持这一点。最终,在他最明确地以基督的名义发布命令时,仍然提出如果违背这个命令,应该如何处理。这似乎表明,在整章中,保罗表达的更多是他个人对可取之事的看法,而非对教会的法律要求。
第十一节中的指示尤其令人注目。保罗重复了主的命令,随后又建议如果女人违背这一命令,她应该避免更严重的违法行为。虽然他在这一点上显然是在立法,但他并没有要求违背命令的人受到任何惩罚。
从这些典型的特点来看,我得出结论:这一章并不是对保罗一贯态度的例外。保罗尽可能避免提出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要求,他更多的是提出原则,并信赖教会内住的圣灵来应用这些原则。在这方面,他显然是个人自由的极端捍卫者。
然而,当个人突破界限,犯下严重罪行时,保罗毫不犹豫地强调纪律的必要性。教会的良知应该在此刻被唤醒,当教会对某个罪行保持沉默时,便是对其道德责任的否定。教会在此时常常反应迟缓。相对较轻的罪行有时会遭到严厉的处罚,而令人震惊的大罪却无人敢于采取行动。
哥林多就发生了这样的罪行。那些写信给保罗求教的哥林多基督徒,对教会中希望过独身生活的成员采取了不作为的态度,并显然没有向保罗提及此事。保罗显然不情愿地介入了此事,但他也显然决定在最后采取行动。然而,他更希望教会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集体行动。在他的书信中,保罗没有直接指示教会应该执行什么惩罚,也没有要求犯错者屈服。他写信指责教会未能履行应尽的责任。根据保罗的观点,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此时有责任为犯错者和自己履行应尽的职责。推卸这一责任是犯罪。因此,保罗等待教会是否会履行责任,而不直接干预。结果,教会响应了他的劝告。犯错者被大多数人逐出教会,他接受了纪律处分,悔改后得到了恢复。
如今,情况有所不同。如果发生严重的罪行,负责该地区的外国神父,会调查此事,可能会与当地委员会合作,并向主教报告。主教审理此案,或接受报告,作出开除教会的决定,并公开宣告。然而,犯错者所属的教会通常不会负起责任,因此教会的处分效果微乎其微。对犯错者的开除几乎没有影响,他能够对外国传教士的严厉判决置之不理,但无法无视邻居教会成员的开除。
我们把逐出教会看作是排除在属灵特权之外;但那些以致招致逐出教会的人,往往是最不感觉到这种排斥的人。在他犯错之前,他的属灵感知已经麻木。他所需要的是教会大多数成员的公开谴责,来唤醒他的良知。如果教会的大多数成员不与他疏远并将他赶出去,那么仅由教会官员单独发出并执行的形式化逐出教会的判决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样的做法不会带来益处;往往还会带来伤害。它使这个人变得更加顽固,而不是让他谦卑。
此外,这样的行为不仅是为了犯错者的益处,也是为了教会的益处。它是为了清除因某个成员的行为而玷污了教会名誉的污点。它意味着要真正清除教会的污点。但如果大多数人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教会的行动,如果他们没有真诚地意识到这一行为是他们的行为,因而不支持它,那么教会的名誉并未得到真正的清除。名义上,这个人被逐出教会;名义上,教会否定了他的行为;名义上,它清除了教会的污点。但如果实际上这只是几个官员的行为,那么在实际情况中,教会并没有清除自己。基督徒和异教徒都明白,教会领导人已经表达了他们的反对,但基督徒和异教徒也同样明白,教会本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哥林多的这个案例中,我们再次看到保罗强调相互责任的原则;他通过在教会认识并执行自己的责任之前,故意不去哥林多,来加强这一原则,确保教会清除了自己与犯错者的共谋。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能理解相互责任这一教义。如果教会的某个成员犯下严重罪行,我们往往无法将责任归咎于教会。我们如此个人主义,以至于无法理解保罗所说的“身体与肢体”的实际意义。在神秘的层面上我们接受它;但当涉及到个人的罪行时,我们自己无法理解,也无法让他人理解他们的真正合一。我们认为,惩罚整个社会因一个人的罪行似乎是不公正的。但东方人更容易理解集体生活的方面。对他们来说,保罗的行为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是中国的教会,保罗责备他们未能逐出一个犯错者,他们不会感到惊讶。但当然,除非教会的集体良知因罪行而真正受损,否则无法实施真正的纪律。那种良知需要被唤醒。通过将责任交给大多数人,保罗唤醒并教育了整个哥林多教会的良知。如果他只是将一封逐出教会的信件寄给长老们,并由他们在教会中朗读,那些效果就不会发生。
因此,他的纪律执行与他行使权威的方式完全一致。正如他呼吁集体良知去制止教会中日益严重的罪恶,他也在争辩、恳求圣灵能启示和坚固他的皈依者;提出原则,并深信圣灵会向他们显明如何应用这些原则,如何使他们有力量去实践它们;在纪律方面,他也为他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但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如何走在这条路上。他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但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步骤。他将责任交给他们,相信他们会学会如何履行这项责任。最终,他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履行责任,他将介入,但这只是他在竭尽全力让他的介入变得不必要之后的最后手段。
因此,他通过“失败”成功,而我们却常常通过“成功”失败。我们实施纪律,却让教会依然不受纪律约束。他实施的是教会的纪律;我们实施的是个人的纪律。他离开了教会,教会仍然摇摇欲坠,但只要坚持他的原则,依然屹立不倒;我们离开教会,教会几乎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与保罗在哥林多所遇到的情形相比,现代传教士的做法是多么不同。当他发现事情的真相时,他的第一反应会是将负责的神父撤职,认为他无能,并任命另一位神父,要求他亲自处理个别犯错者。错误会通过权威得到纠正,但原则仍然未知,也未被教授。
我知道有人会说这是一个荒谬的比较,我们的东方皈依者就像婴儿一样,谈论原则并让他们去找出如何应用这些原则几乎是在自取灭亡。但这种论点,虽然对强势人物来说非常方便,却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有力。东方人并非如此幼稚。他们能够理解原则,在许多方面比我们更理解集体责任。即使他们是婴儿,婴儿也只能通过行使他们的婴儿能力来得到真正的教育。依赖不会培养独立;奴役不会教育人们获得自由。此外,他们还有圣灵的帮助来加强和引导他们。基督徒不仅仅是凭借本性而存在,他们是一个充满圣灵的身体。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对他们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对圣灵的信心。我们过于关注皈依者的天性,而保罗关注的是他们在恩典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