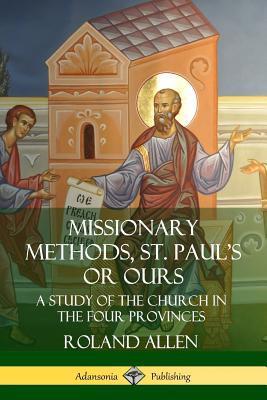本文译自书籍 “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A STUDY OF THE CHURCH IN THE FOUR PROVINCES
BY ROLAND ALLEN(FORMERLY MISSIONARY IN NORTH CHINA)
第二部分 福音的宣讲
V. 圣保罗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拥有行神迹的能力?
VI. 圣保罗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财务安排?
VII. 圣保罗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宣讲方法?
五、关于神迹
神迹在圣保罗在“四个省份”传教的记述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有人认为神迹的存在使圣保罗的传教方式与当今的传教工作毫无或几乎没有关联,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这些神迹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圣保罗如何利用它们。事实上,与其说神迹削弱了对比的有效性,不如说圣保罗对神迹的使用为我们今天许多形式的传教工作提供了一些具有恒久价值的原则。
在“四个省份”的五个城镇中,有关于圣保罗行神迹的记载。在以哥念,记载说:“主借着他们的手行神迹奇事,证明祂恩典之道的真实。”在路司得,圣保罗治愈了一名瘸子。在腓立比,他驱逐了一个具有占卜能力的邪灵;在以弗所,“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神迹,甚至人把他身上的手巾或围裙拿去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恶鬼也出去了。”最后,在特罗亚,他复活了犹推古。
犹推古的复活显然是一个特殊的神迹,无论是从事件的性质还是其发生的环境来看。这并非旨在促进福音传播的神迹,而是为信徒提供安慰。因此,这个神迹更类似于彼得复活多加的事件,而不同于其他关于圣保罗的神迹记录,因此不纳入此次讨论范围。在安提阿、特庇、帖撒罗尼迦、庇哩亚和哥林多,与福音宣讲相关的神迹未曾在《使徒行传》中提及。
由此可见,神迹在圣保罗传教工作中的重要性可能被过分夸大了。它们并非他传教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吸引信徒的影响力也并非我们常以为的那样大。拉姆齐教授甚至指出:“《使徒行传》中记录的奇事通常并未被描述为对传播新信仰有显著效果。”的确,只有在以弗所,神迹与信徒的显著增加有明确联系;而至少在一个案例中,神迹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阻碍。
然而,从整体来看,圣路加的叙述并未给人留下圣保罗的神迹不利于福音传播的印象。在帕弗斯,一个神迹导致了一位重要人物的皈依;在以哥念,神迹奇事见证了福音的真实;在路司得,一个神迹为教义的阐释提供了良机;在以弗所,神迹成为赢得重大属灵胜利的手段。圣路加提到这些神迹时,并未暗示它们对福音传播无效,反而将其描述为圣保罗事工中自然且适当的一部分。他也并未记录圣保罗的所有神迹;我们知道圣保罗在哥林多行过“神迹奇事和大能”(参《哥林多后书》12:12),而圣路加仅选择了一些典型事例加以记录。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拉姆齐教授观点中的核心真理揭示了一个重要原则:圣保罗从未利用这些神迹来诱导人们接受他的教导。他并未通过承诺治病或借治病吸引人来听他的讲道。圣路加似乎刻意避免给人一种印象,即神迹可以用来吸引人们皈依基督教,只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益。我们从未被告知圣保罗通过治病的神迹直接使某人皈依。的确,路司得的瘸子似乎是个例外,但故事中明显暗示他在被治愈前已经是某种程度的“听道者”,他的皈依并非因神迹直接引发。类似地,我们也未被告知腓立比那个占卜少女的皈依。尽管莱特富特主教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她皈依了,但这仅是一种推测,并非必然结论。圣路加仅提到她承认使徒是“至高神的仆人”并且被治愈。我们或许会认为这样的经历必然导致她的皈依,但圣路加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
圣保罗并没有通过行神迹来使人皈依,也没有试图以神迹吸引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他没有通过提供医治的条件来换取人们听从他的教导。在这一点上,他展现了一条原则,这条原则也指导着早期教会在施行慈善时的方式。正如哈纳克教授所言:“我们并不知道有任何案例显示基督徒通过施舍的方式希望吸引或实际吸引了追随者。”
我不得不认为,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非常谨慎遵守的原则。在印度传教的早期,我们的传教士曾通过向学生支付定期报酬,来吸引他们进入学校接受基督教教育。结果并不理想,这种做法也已被全面放弃。但我们现在有时仍会以提供世俗教育或医疗服务为诱因,吸引人们接受我们的宗教教育或影响。这在原则上与支付金钱类似,只是形式上没那么严重。我不禁认为,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将任何物质诱因视为不符合健全教义的行为,正如我们现在认为早期直接支付金钱是不合适的一样。
然而,尽管圣保罗没有以医治作为吸引人接受教导的手段,他行神迹的方式却对其宣讲福音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神迹吸引了听众
神迹通常是针对群众而非个体的。例如,在路司得如此,在圣殿的美门前如此,其它地方亦然。神迹奇事吸引人们前来观看圣保罗是谁,自然也激发他们的兴趣,想要听听他要说什么。因此,神迹为福音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2) 神迹被普遍视为神圣认可的证明
神迹通常被视为神灵对行神迹者的认可。例如,塔西佗在记载维斯帕西安于亚历山大行的神迹时提到,这些神迹被视为神对他的恩宠与眷顾的标志。同样,圣路加强调圣保罗在以哥念所行的神迹,是“主为他恩典之道所作的见证”。在犹太人中,耶稣自己也多次以其作为证明其权柄的依据。尼哥德慕承认:“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在基督徒和外邦人之间,神迹的力量都是不容置疑的。
(3) 神迹展现了耶稣对异教神灵和恶魔的胜利
圣保罗的神迹(除了复活犹推古外)几乎都发生在异教背景中,目的是向外邦人而非犹太人或基督徒彰显基督的能力。例如,在以弗所和帕弗,圣保罗与以吕马和以弗所的术士展开了对抗,最终展示了耶稣的能力远胜异教的神灵与魔法。正如摩西在法老面前彰显耶和华战胜埃及诸神的能力一样,圣保罗的胜利也表明了耶稣的灵胜过异教的邪灵。
(4) 神迹是新宗教核心教义的行动演示
圣保罗的神迹不仅仅是能力的彰显,更是对基督教两大核心教义——慈爱与救赎——的直接诠释。慈爱,即对软弱者和受压迫者的怜悯,以及在行动中体现的爱心,是基督及其使徒们教导并践行的根本。圣保罗出于对受压迫者的怜悯或对信仰萌芽的敏锐洞察,施行了医治和驱魔,从而体现了福音的解放力量。
早期教会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逐渐以其有组织的慈善事业闻名于世,包括抚养孤儿寡妇、关怀病弱残疾者、帮助奴隶、探望囚犯以及援助遭遇重大灾难的人们。两百多年后,德尔图良在总结基督徒慈善行为时写道:“正是这种高尚的爱心行动,吸引了许多人对我们投以关注。”毫无疑问,这种慈善精神对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
同样地,圣保罗的神迹彰显了释放与救赎的教义。在使徒们传播新信息的那个世界中,宗教并不是疲惫者的慰藉,病者的良药,罪人背负重担时的力量,或无知者的启蒙。宗教是健康者和受过教育者的特权。病人和无知者被排除在外,他们被邪恶的恶魔束缚着。“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这是犹太人和希腊人普遍的教义。哲学家们只向富裕、有知识和纯洁的人传道。只有手洁心清、智力健全的人才能被邀请参与奥秘仪式。对于异教徒来说,基督徒竟然呼召病人和罪人,这始终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他们说,凡是罪人,无知之人,孩童,或者更广泛地说,凡是不幸之人,神的国都会接纳他。难道你不认为那些不义之人、窃贼、夜贼、投毒者、亵渎圣物者、盗墓者也是罪人吗?如果一个人在发布强盗集会的公告,他还能邀请谁呢?”然而,在那个时代,人们逐渐感到需要一种宗教来寻求医治和救赎。对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作为“救主”的信仰已经在人们中广泛传播;其他神也被称为救主。“现在,”哈纳克说,“一个神若不被认为是救主,就不可能再是神。”人们已经准备好接受一种救赎的教义。使徒正是迎合了这一需求而宣讲。“我们救主神的慈爱已向全人类显现。”他的宣讲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的信徒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但的权势归向神。”在一个被罪恶、苦难和死亡压迫的世界里,他怀着耶稣的灵来到,周游各地行善,医治一切被魔鬼压迫的人。他的神迹是向全世界展示其教导性质与目的的可见标志。这些神迹宣告耶稣是被掳者的解救者,病人的医治者,疲惫者的慰藉,以及受压迫者的避难所。
毫无疑问,这种行奇迹的能力,这种展示耶稣对邪灵权柄的显著表现,在早期教会中被视为用以驳斥反对者、说服犹豫者的极其重要的武器。“基督徒以驱魔者的身份进入这个大千世界,”哈纳克教授说,“驱魔是他们传教宣传中非常有力的一种方式。”每位基督教护教者都将其视为基督教优于异教宗教的显著证明。异教徒诉诸神迹、神谕、奇兆来证明诸神的存在;而基督徒则以驱魔作为基督神性及其对所有异教神灵和恶魔的至高权威的证据。
这种能力在教会中极为珍视,并深受信徒渴求。但它的重要性容易被高估,而显然圣保罗也看到了这一危险,并予以反对。他并未将行神迹的恩赐置于圣灵恩赐的最高地位。他并未暗示他的最佳工人都拥有这种能力。在他眼中,重要的不是行神迹的能力,而是激励生命的灵。神迹之力不过是圣灵众多表现之一;其中至高无上的是爱之灵。在他看来,医治的方式——是否即刻通过一句话完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灵与大能的彰显。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吸引人、打动人、转变人的并非强大能力的拥有,而是使用任何能力时所表现出的精神。如果我们不再拥有他那样的能力,我们仍应拥有激励他的那种灵。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彰显圣灵;有足够的能力吸引听众;有足够的能力证明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有足够的能力让寻求者确信基督教优于所有异教宗教;有足够的能力通过行为展示我们宗教的特性,其救赎与爱,只要我们愿意用这些能力揭示圣灵。有一天,也许我们会重新找回对神迹的早期信仰。然而,目前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神迹就认为第一世纪和今天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认为使徒的方法不适用于我们的传教。如果那样说,就是将形式置于精神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