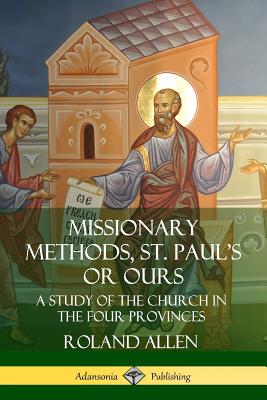本文译自书籍 “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A STUDY OF THE CHURCH IN THE FOUR PROVINCES
BY ROLAND ALLEN(FORMERLY MISSIONARY IN NORTH CHINA)
四、道德与社会状况
圣保罗建立教会的地方,都是罗马和希腊文明的中心。然而,当我们谈论希腊-罗马文明时,通常想到的是伟大哲学家的崇高教义,并想象一个被这些教义渗透的世界。然而,实际上,帝国内并没有统一的文明标准。这些大城市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以及处于文明或野蛮不同阶段的各种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如同今天的卡菲尔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差异一般巨大。比格博士(Dr. Bigg)指出,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状况,只能与克莱夫(Clive)和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征服后的印度相提并论。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圣保罗在四个省份建立教会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有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圣保罗传教对象的社会状况或许能解释他在建立教会上的成功;然而,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圣保罗的大部分皈依者出生并成长在一个道德环境绝不比今天的印度或中国更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恶劣的氛围中。
当然,也存在崇高的哲学,深奥的宗教奥秘,以及像狄翁·克律索斯托莫斯(Dion Chrysostom)游历中遇到的那些朴素而虔诚的宗教信徒。在各个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无处不在;但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圣保罗时代四个省份的宗教和道德状况。他们就像中国的张之洞并不能代表满清官僚体系,或图尔西·达斯并不能代表印度教徒,或者阿尔弗雷德大帝并不能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撒克逊人一样,无法作为典型代表。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与当时帝国的宗教生活之间的距离,正如塞涅卡的哲学理论与他自身实践之间的距离一样遥远。
弗里德兰德(Friedlander)对早期几个世纪的文学和纪念碑所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对比:
“文学作品主要出自不信教者、漠不关心者,或那些试图通过反思和解释来精神化、净化或改造大众信仰的人之手。另一方面,纪念碑在很大程度上则起源于那些较少受到文学及其主流趋势影响的社会阶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见证了一种积极的多神教信仰,这种信仰既没有疑虑,也没有精巧的解释。”
当然,我无法在这里全面描述这些省份的道德和社会状况,但要正确理解圣保罗的工作,必须记住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四个重要方面:
- 对恶魔的普遍信仰
“在困境中,异教徒自然会转向恶魔崇拜。”
“不仅仅是偶像崇拜,而是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恶魔的支配;它们坐在王座上;它们徘徊在摇篮旁;整个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地狱。”
“整个世界都卧在恶者之下。”
这种信仰不仅存在于野蛮人或弗里吉亚人中,还存在于罗马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中——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相信恶魔的普遍力量。不仅是未受教育者,连最有文化的人也深信不疑,这与今天的中国人或贡德人(Gonds)对恶魔的普遍信仰无异。这种信仰的后果在当时与今天相同——带来了身体和心理的疾病、残忍、奴役和堕落。
像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这样的人认为,将通奸和纷争归咎于神,并相信盗窃和犯罪之神是极大的不敬,但他却相信一些最恐怖的巫术形式。人祭并非闻所未闻,而对巫术的信仰普遍存在。受过教育的人相信,任何敌人都可以通过咒语在暗中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
普鲁塔克(Plutarch)是一位善良且有学问的人,但当谈到那些与不祥和邪恶日子相关的仪式时,例如生肉的吞食、身体的残害、斋戒和捶胸、祭坛前的淫秽喊叫、狂暴和癫狂时,他很认真地认为,这些仪式并不是为了崇拜任何神,而是为了取悦并驱赶恶魔。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才出现了许多最近发现的魔法咒语,其中的公式可能就填满了那些在圣保罗传教影响下在以弗所被焚烧的魔法书籍(价值五万德拉克马)。
从这种迷信的根源,衍生出了铅板、骨头碎片、对梦境和预兆的信仰、神奇的爱情药剂、被灵体带走的儿童墓志铭,简而言之,是整个低劣迷信的世界。当我们阅读哲学家的论文时,我们想到帝国中的宗教,就像我们阅读埃德温·阿诺德爵士(Sir Edwin Arnold)或贝赞特夫人(Mrs. Besant)的著作时想到东方的宗教。当我们听到比格博士(Dr. Bigg)告诉我们,“认为恶魔崇拜是帝国广大民众的实际宗教,或许并非过于苛刻的说法”时,我们想到的帝国宗教,犹如阅读科普斯顿博士(Dr. Copleston)对锡兰佛教的描述,或德·格鲁特教授(Professor de Groot)对中国宗教的叙述时想到的东方宗教。德·格鲁特教授对中国宗教的性质持最低的评价,但他对中国恶魔崇拜的章节,可以直接纳入比格博士或弗里德兰德博士(Dr. Friedlander)关于帝国大众宗教的描述中,而不会改变这些描述对我们的总体印象。
在皈依之前,圣保罗的每一位听众都出生并成长在这种迷信恐惧的氛围中;甚至在皈依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熟悉偶像”,并且未曾完全停止对恶魔的信仰。圣保罗及其他使徒的传道并非否定这种信仰;相反,它为接受这一信仰的人提供了无敌的武器,用以对抗邪恶的军队,但并未否认这些军队的存在。唯有对基督之灵无时不在的意识,才让基督徒能够将这些恶魔驱逐出自己的内心和生活的世界。解脱并非通过否定而来,而是通过战胜而得。我想顺便提到,在异教地区,也许更明智的方式是不断宣讲基督对一切属灵和物质的至高无上,而不是否定或嘲笑这些灵体的概念。一些传教士知道,而其他传教士也应该了解,让一个人隐藏他对恶魔的信仰比根除这种信仰要容易得多。否认恶魔的存在或嘲笑信仰它们的人,并不能帮助我们的皈依者战胜恶魔,只会让他们隐藏自己的恐惧。通过宣讲基督的至高无上,我们才能为他们提供真正的解药,带去一位真正的救主,在他们黑暗的时刻给予帮助。
考虑圣保罗在四个省份的工作时,第二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宗教仪式的道德特征。有些宗教奥秘无疑可以被赋予高度道德的解释。哈纳克(Harnack)在两三页中收集了希腊化与东方主义交融为福音传播铺路时的最重要的思想和宗教倾向:
- 灵魂与身体的明确区分,以及对灵的独特重要性的强调;
- 上帝与世界的明确区分,以及对神性不可思议、不可描述但伟大而善良的承认;
- 对物质世界和肉体的贬低;
- 对从世界、肉体和死亡中获得救赎的渴望;
- 相信救赎依赖于知识与赎罪;
- 相信永生可通过回归上帝获得,并且途径可寻;
- 相信追求者可以通过启蒙获得带来救赎的秘密知识。
“灵魂、上帝、知识、赎罪、禁欲主义、救赎、永生,再加上用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取代民族主义——这些是当时活跃而有影响力的崇高思想……凡是真正活跃的宗教,都是在这一思想与存在的圈子中呼吸。”
他继续说道:“生活在这一思想圈子中的实际人数毫无意义……宗教史中,真正涉及活跃宗教的部分,总是在非常狭窄的轨迹中运行。”
然而,对我们当前的探讨来说,生活在这一圈子中的人数是至关重要的。一些选定的灵魂在得墨忒耳(Ceres)、伊希斯(Isis)或居比路斯(Cybele)的奥秘中理解到了精神意义;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仪式并未传达深奥的真理,就像流浪祭司的舞蹈和自残行为并未向村民传达关于罪与救赎的深刻真理一样。他不过是带着小神龛和偶像在村庄间游走,进行一场赎罪的表演,同时为自己募捐而已。
寺庙中举行的宗教仪式,无论是其崇拜对象的肮脏,还是崇拜过程的淫秽,都令人难以言表。对于这些神明的传说,就像对奎师那化身的故事一样,几乎无法引用;而这些崇拜的附带情况,也只比所奉献神灵生活的污秽稍好些。可以说,以弗所和哥林多的神庙,与贝拿勒斯或北京的庙宇一样,绝非美德之家。《以弗所书》中圣保罗的语言,正好描述了他的皈依者所来自并居住的环境。
正是基于迷信和污秽这两种现象,几乎所有关于我们现代在异教地区开展传教事业的方法论论据得以确立。然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不论圣保罗的传教方法有何优点,其背景并非建立在社会和宗教条件优于我们现代传教所面对的环境之上。
第三个因素:奴隶制与角斗场
除了上述两点,还有两个当时的罪恶,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已不复存在:奴隶制和角斗场。关于角斗场的表演,那些残忍的娱乐,所有人都非常熟悉,这里无需赘述。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注意,即便是当时最优秀的人,对这些非人道的表演所持的态度也令人震惊。比格博士指出,“异教作家中仅有三处文字表达了对这些表演稍显充分的谴责。”弗里德兰德进一步补充道:“在所有罗马文学中,几乎找不到今日对这些非人性化愉悦所产生的那种强烈厌恶。”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此表现出完全的漠不关心。
像普林尼和西塞罗这样的人物甚至为这些表演辩护,称其“虽然可能对耳朵没有教益,但对眼睛而言是出色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痛苦和死亡的承受力,并激发对死亡的蔑视和对荣耀创伤的热爱。”连马可·奥勒留也只是对这些表演感到厌倦,抱怨“总是千篇一律”;而作为异教美德的典范,辛马库斯却因某些撒克逊人自杀于牢房、拒绝在公众面前互相厮杀来完成他为庆祝儿子担任执政官而筹备的表演,愤愤不平。
极度吸引力的案例:阿吕庇乌斯的故事
这些表演对那些自认为超越此类诱惑的人所产生的非凡吸引力,可以通过阿吕庇乌斯的著名故事得到最佳诠释。
阿吕庇乌斯被一些大学好友强行拖入了角斗场。他愤怒地说道:
“如果你们强行把我带到这里并让我坐下,你们难道还能强迫我的眼睛注视,或强迫我的心灵关注这样的表演吗?我的身体或许在场,但我的精神将会远离,我将战胜你们和这些表演。”
当他们找到座位后,他紧闭双眼,拒绝让思想与这些罪行纠缠。他心想:如果耳朵也能堵住就好了!然而,在某场战斗的一个回合中,全场观众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他被好奇心战胜,自信无论发生什么,即便看到了也能轻视并遗忘,于是他睁开了眼睛。然而,他的灵魂瞬间遭到比那位格斗士所受的肉体重创更为致命的伤害。他的堕落比角斗士的倒下更加悲惨,而正是那贯穿耳膜、打开双眼的欢呼,最终将他的灵魂暴露在致命的打击之下……
因为看见鲜血,他吸收了冷酷无情;他不再转头回避,而是目不转睛地凝视,毫无察觉地饮下了愤怒的毒酒。他被战斗的喧嚣深深吸引,为杀戮的狂喜所陶醉。他不再是刚刚到来的那个阿吕庇乌斯,而是变成了他所加入的群众中的一员,甚至成了那些带他来的人无意中培养出的铁石心肠的共犯! 我还需要多说什么呢?他凝视着,呼喊着,狂热着,带着一种驱使他再次前往的疯狂回到家中,不仅和那些最初拖他去的人一起回去,还反过来拖着其他人加入。
特土良说:“没有人能够享受这样的娱乐而不受到其强烈的刺激;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刺激中而不陷入其自然的堕落。”
这些表演带来了两个极其灾难性的后果:
- 它使所有人都清楚地记住了人类分为两个阶级:有权者与无权者,这是奴隶制最大的祸害。
- 这种刺激使所有其他更理性、更健康的娱乐形式显得苍白无力,尤其对剧场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由于竞技场和角斗场的强烈刺激,舞台为了吸引观众只能依赖卑劣的手段,比如粗俗的笑话和感官性的低俗表演。剧场中没有什么是过于粗鄙的,也没有什么是过于猥亵的,甚至连最神圣的内容都可以被恶搞。”神话传说中的诸神故事经常成为最恐怖、最堕落场景的题材。“例如,当美少年巴蒂勒斯起舞时,最放荡的滑稽演员莱达在看到如此精湛的感官艺术后,都自觉像个乡下来的菜鸟。”
阿普列尤斯描述了一场他在科林斯节庆上看到的皮吕克舞剧:
舞台上伫立着一座高大的木制山峰,模仿伊达山,覆盖着树木,清泉从山上流淌而下。一些山羊在草地上悠闲觅食,巴黎斯(特洛伊王子)身穿飘逸的长袍,头戴王冠,扮作牧羊人。不久后,一个扮演墨丘利(赫尔墨斯)的美少年登场,他身上唯一的衣物是一件披在左肩上的斗篷。他手持一枚金苹果,优雅地舞步至巴黎斯面前,将苹果交给他。接着,一位头戴白色王冠、手持权杖的女孩出场,她的装扮表明她是朱诺(赫拉)。随后,另一位女孩登场,显然是密涅瓦(雅典娜),因为她头戴发光的头盔,头盔上环绕着橄榄枝。她高举盾牌,挥舞长矛,如同战斗中的女神。
最后,维纳斯(阿芙洛狄忒)以超凡的美丽与优雅登场,她几乎全裸,只以一条透明的蓝色轻纱覆盖身体。微风轻拂她的纱衣,展现出两种鲜明的色彩——白皙的肌肤与蓝色的薄纱,仿佛表明她来自天堂,又从海中升起。
朱诺在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的陪伴下以优雅自然的舞蹈示意,她愿将亚洲的统治权赐予巴黎斯,只要他将金苹果奖给她。接着,密涅瓦伴随恐惧与惊惶之神,挥舞利剑,气势逼人,通过热烈的肢体动作暗示她将赐予巴黎斯卓越的勇武之名。
最终,维纳斯以甜美的微笑走到舞台中央,受到观众热烈欢呼。她被一群精致而可爱的男孩簇拥着,他们就像刚从天堂或大海中飞来的爱神邱比特。这些男孩手持弓箭与火把,仿佛为她点燃了通往婚宴的道路。当柔美的吕底亚曲调从长笛中缓缓流出时,全场观众陶醉不已。而维纳斯随音乐翩翩起舞,那舞蹈显然令阿普列尤斯着迷,他特别注意到她的眼神变化:一会儿流露出慵懒的柔情,一会儿闪烁出炽热的激情。阿普列尤斯写道:“她似乎只用眼睛在舞蹈。”
维纳斯随后来到裁判面前,以手臂的动作许诺她将赐予他如她般超凡美丽的新娘。于是,裁判欣然将手中的金苹果递给了她,象征胜利。裁决之后,愤怒而沮丧的朱诺和密涅瓦以激动的动作表达不满后退场。而充满喜悦的维纳斯则与她的合唱团一起舞动,庆祝胜利。
弗里德兰德指出,这些以经典为主题的表演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太过高雅复杂。受过教育的人主要倾向于欣赏哑剧,而普通群众更喜欢粗俗喧闹的滑稽戏与猥亵表演。
无论是在竞技场、角斗场还是剧场,这些娱乐活动的道德影响都令人难以想象。我们往往习惯于美化过去,很难相信描述中所提及的恶行。我认为,只有在与异教社会长期密切接触后,才能真正理解这些事物的意义。
不过,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无法找到类似的平行事物。虽然有些低劣的宗教戏剧存在,也有表现神明的节目,但这些神明的超凡特质主要体现为恶行。然而,已不存在角斗表演,也不再有罪犯被投喂野兽的场景。
最后,当时的奴隶制度与我们已知的奴隶制截然不同,但并不是更好的存在。罗马帝国中的奴隶通常与主人拥有相同的肤色,甚至可能同种族、同文化,教育程度也常常相当。今天是奴隶的人,若明天被解放,他们便能毫无障碍地融入主人所在的社会圈层,而不会因种族、习俗或文化差异而被排斥。
这或许可以与今天中国的奴隶制度作对比。在中国,奴隶与他们的主人肤色相同、种族相同,但他们总是属于最低阶层,通常完全没有教育。大部分奴隶是女性,而且这一阶层的奴隶数量不多。然而在罗马帝国,男性奴隶的数量占压倒性优势,而且他们的数量令人震惊。不仅在一些大户人家的奴隶人数庞大,而且在一些城市中,几乎没有家族中有奴隶血统的人。科林斯就是由凯撒用解放的奴隶来殖民的。帝国城市的整个社会结构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且深深渗透着奴隶制的特有弊病——奴性与傲慢。
虽然在这个时期,城市中的奴隶条件有所缓解,他们通常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得到友善对待,但他们依然没有任何权利。女性、女孩和男孩没有任何保护,主人意志是他们唯一的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层,许多富裕的绅士为了去除鞭打留下的伤痕,会花大笔钱请医生治疗,或者用昂贵的药膏掩盖这些伤痕,以免让宾客看到。
现在请稍作考虑这些条件对圣保罗所接触到的人的教育影响。从出生起,孩子就由一位奴隶保姆照顾,这些保姆“通常沉浸在最粗俗、最可怕的迷信中。”当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他由一位奴隶教师照看,而这位教师的兴趣是迎合年轻主人的恶习,掩盖他的不当行为。孩子通常会进入由解放奴隶经营的私立学校。在那里,他接受的教育,被比格博士称为“设计得极其精妙”。这些学校中最好的教育系统,“可能比我们自己学校的教育系统要好得多,甚至可以追溯到阿诺德博士时代”,但它完全是异教式的。
虽然许多最好的古典作家将神明的传说视为纯粹的传说,而在英格兰,孩子们阅读朱庇特、维纳斯和埃斯库拉比乌斯的故事时,并不觉得它们有什么真实感,就像他们读《蓝胡子》的故事时没有感觉到任何真实性一样;然而,圣保罗时代的孩子却处境截然不同。他们在科林斯读到关于维纳斯的故事时,正身处维纳斯神庙的阴影之下,神庙中有一千名祭司,所有人都知道她们的欺诈和伎俩。他们读到埃斯库拉比乌斯的故事时,知道如果自己生病,父母会去埃斯库拉比乌斯神庙奉献祭品,祈求康复。他们在以弗所读到关于戴安娜的故事时,知道银匠们在那里贩售她的神像,而那尊从朱庇特降下的污秽神像也安放在那里。
他们知道得太多;而家庭的影响则一如往常,远非应有的样子。即便是好老师,也难以抵消保姆、教育者和父母的负面影响,而且并非所有教师都是好教师。
当孩子离开文法学校后,如果有条件,他会去学习修辞学,在那里他学会在任何情况下优雅、流利且至少看起来充满学识地表达任何话题。学校会给出固定的题目和角色,学生在这些题目和角色下展开讨论。他们不仅学会批评通奸者、拉皮条者和赌徒,也学会为他们辩护。他们还学习如何做出精细的文学判断。然后,他们带着这些关于神明的历史和人的性格的知识,带着一种对恶魔的恐惧感,作为唯一的强烈宗教影响(如果还有宗教影响的话),走向世界:去看竞技场、马戏团和剧场,在这些地方,他会发现各种刺激自己动物天性的事物;去参加节日的庙会,发现这些庙会充满了骚乱;而奴隶们总是随时在旁,准备为他服务,满足他最微小的愿望。圣保罗十年内所接触的每个有教养的人(除了犹太人)都曾受过这样的教育,读过这样的文学,参观过这样的神庙,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曾观看过那些角斗表演——每个圣保罗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孩子都经过了同样的训练。
如果希腊的道德氛围已经堪忧,那么小亚细亚的情况则更加糟糕。当地宗教的性质“使得希腊教育相比之下显得纯净,希腊的道德家、哲学家和政治家都曾严词抨击弗里吉亚宗教,认为它是希腊生活理想的最大敌人。”希腊社会和生活至少是以婚姻为基础,而小亚细亚的宗教则将“任何基于婚姻的有组织和稳定的社会生活视为对自由、无拘束的自然神圣生活的亵渎,这种生活在伟大女神的宠儿——野生动物中得到体现。”
当然,这不是对圣保罗传教所在的各省社会状况的完整描述,但这些因素确实存在,而且我们如果要正确理解使徒所面临的任务的性质,就不能忽视它们。恶魔崇拜、不道德的宗教仪式、角斗游戏、奴隶制——这些问题不能被置之不理。一个人如何能在认为自己朋友身上有恶魔的情况下正确地对待他?当麻烦来临时,一个人如何能通过向恶魔祈祷来追求正直?当他所了解的神明都被描述为最卑劣的生物时,一个人如何能保持对神的真实奉献与虔诚?当他和他周围的每个人都认为某些人(最庞大的那部分人)根本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的主人的话即为唯一的“对”,他们仅仅是为了给主人提供服务和娱乐,无论是通过生命还是死亡而存在时,一个人如何能够行走正道?
哈纳克教授告诉我们,“认为早期教会曾经关注过‘奴隶问题’是一个错误。原始基督徒看待奴隶制的态度与他们对国家和法律关系的态度并无不同。他们从未想着要废除国家,也没有想到要出于人道或其他理由废除奴隶制——即使是在他们自己内部。”在圣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中,大量的会众是奴隶,其中一些人也是奴隶主。基督徒主人被劝告要宽容,基督徒奴隶则被劝告要忠诚。没有“奴隶问题”的存在,恰恰突显了这一制度的普遍接受。众所周知,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奴隶制存在,那些条件总是一样的;在没有任何种族或习惯性障碍的情况下,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尤为明显。
无论帝国在教育、文明、哲学或宗教方面拥有多少优点——只要它被奴隶制、竞技游戏、庙会和巫术所污染——我认为无法辩驳圣保罗的教徒们在道德方面所受的社会教育,比今天我们教徒所受的教育有任何特别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