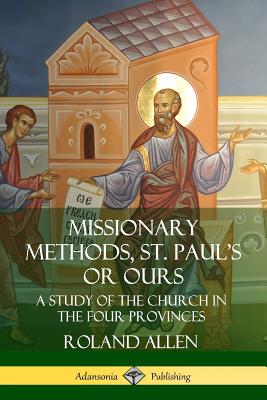III. 阶层
在当今时代,人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国家中某些特定阶层的重要性,以便更有效地传播福音。在中国“自然足会”(“Natural Foot Society”)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过明智地吸引有影响力的阶层所能取得的惊人成果。这一运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发起者并未将时间浪费在向村庄中无知且保守的农民传教,而是首先争取开明且富有的官员和商人家庭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从少数外国人发起的运动在十到十二年的时间内得以在中国牢固确立,并且不再需要外国的鼓励和支持。
同样,对特定阶层在实现某些目标方面价值的认识,促使了诸如“基督教学生运动”(the 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这样的组织的建立。这一思想实际上也贯穿于几乎所有针对外国的教育传教活动,以及针对官员阶层的特殊传教活动。此外,在另一端,我们经常被告知,在印度,我们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在提升被压迫的贱民阶层上,因为这一群体的复兴和文明化将对其他社会阶层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有一种常见的解释认为,使徒保罗在四个省份传教的成功与他遵循这一方法有关。人们说,在这四个省份中,有一个特别适合接受并确立福音的特殊阶层。同时也有人以此为理由反对在现代条件下运用保罗的方法,认为如今这种特殊阶层已不复存在,而我们的信徒也不具备他那个时代信徒所享有的特殊优势。因此,有必要探讨他是否确实主要针对某个特殊阶层传教,以及来自该阶层的信徒是否足够多,以至于使我们有理由因为他的这种方法是在特殊情况下应用于特殊人群而拒绝效仿他的传教策略。
是否可以主张,圣保罗通过将某些特定重要阶层的才能和影响力纳入基督教的侍奉,成功地在四省建立了基督教?这似乎并非如此。圣保罗总是从会堂开始他的工作,向犹太人和敬畏上帝的希腊人传道。然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都未能为他提供这样的阶层。很快就显而易见,基督教无法在犹太人的土壤中生根。基督教精神更与希腊人思想的自由相契合,而非犹太人思想中狭隘的律法主义。基督教的内涵过于宽广,无法被犹太教的枷锁所束缚。从一开始,它就被生于其中的民族所排斥,转而在异国他乡找到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将生命带给它所传达的对象。
圣保罗的确在会堂传道,但他很快被禁止在那里继续讲道,也没有许多犹太人跟随他。这里没有必要详细探讨圣保罗在四省建立教会的历史,也无需详细研究他致四省教会的书信,因为关于这些教会几乎完全由希腊皈依者组成这一点,学术界几乎完全一致认同。圣路加一次又一次地强调,犹太人顽固地拒绝,而希腊人却热切地愿意聆听圣保罗的教导。圣保罗也多次提到,他的信徒是曾亲身经历过偶像崇拜的人。
然而,圣保罗对犹太人的传道尝试不仅大多未能成功,还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些尝试不仅通常导致他本人及其信徒遭受暴力攻击,还使他的工作突然中断,他不得不逃离因其激怒众人而引发的愤怒;同时也凸显了一个困扰我们至今的问题:他自己权威的真实性以及其信息的可信度。圣保罗以犹太人的身份和犹太教的一种形式的教师身份进入各城,他声称所传的启示是由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赐予人类的。他宣布,犹太人的弥赛亚已经降临,并显明自己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全人类的救主。然而,他一传递这一信息,整个犹太社会便起来反对他,将他驱逐,并试图以亵渎神明的罪名取他性命。
如今,阻碍我们传教的最大障碍在于那些自称基督徒、却对基督教表现出实际否认的同胞的冷漠;而对于圣保罗来说,由本国宗教领袖对他的暴力迫害无疑是更大的绊脚石。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足以证明他信息的虚假。从耶路撒冷到伊利里库,圣保罗传扬了福音,但从耶路撒冷到伊利里库,这福音却被那些本应最有资格判断其真实性的人全盘否定。当圣保罗转向外邦人时,可能在许多人看来,他是放弃了说服那些真正了解拿撒勒人耶稣的犹太人的尝试,而转而向那些不了解的人传播被那些知情者轻蔑拒绝的信息。
如果圣保罗没有从会堂开始传道,这一困难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当犹太人看到那些曾在会堂敬拜的人们追随圣保罗时,他们“心生嫉妒”,开始反驳并亵渎他的言论。毫无疑问,这一困难必然存在,无法避免,但圣保罗在会堂中的传道却让这一困难立即以最激烈的形式爆发。
因此,圣保罗被迫公开宣告他与犹太人之间的分裂,在会堂中宣布他已与犹太人决裂。这一趋势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显著,直到他采取了一项极具象征性的行动:在会堂隔壁开设了自己的传道场所。这一行为乍看之下似乎是有意挑动其同胞的情绪,很难理解为何圣路加如此细致地记录了此事,除非他认为这标志着圣保罗与犹太人之间、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关系的一次明确进展。
为了让希腊人能够正确地理解基督教,圣保罗有必要强调基督教并非犹太教的一个教派,它的真伪完全独立于犹太当局对其的态度。因此,有理由认为,圣保罗最初在会堂传道,既是出于宗教责任感,也是出于某种策略考量。这似乎可以从他在安提阿和哥林多的会堂中说的话,以及他在《罗马书》中对犹太人的总体态度中看出端倪。在会堂传道可能是一种宗教义务,但它显然并非没有弊端。圣保罗可能认为他欠犹太人的债,但很难说他有意将犹太人作为一个阶层来转化。
尽管圣保罗在会堂中并没有吸引许多犹太人皈依,但他从会堂中吸收了一些皈依者,而这些皈依者对教会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和敬畏上帝的希腊人为教会注入了对教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元素。他们已经确立了关于上帝独一性的信念,并认识到了偶像崇拜的愚蠢。他们还理解道德对真实宗教的重要性,并且熟悉公共礼拜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对《旧约圣经》有一定的了解。圣保罗不仅将《旧约圣经》作为争辩的教材,他还在将它从属于犹太民族的范畴转移到属灵上归属于“新以色列”的范畴。他已经将撒拉和夏甲的故事视为寓言,将割礼解释为属灵的仪式而非肉体的仪式,并宣告亚伯拉罕为所有信徒之父。至少一些敬畏上帝的希腊人已准备好接受、理解并传播这些观念。
与此同时,也不应夸大这些人在教会中的影响。他们的数量不可能很多,因为圣保罗提到,他的教会中的大多数基督徒都曾是偶像崇拜者。《帖撒罗尼迦书》要求的理解不需要熟悉《旧约圣经》,而书信中的道德警告则针对了异教文化中的普遍恶习。因此,如果我们假设会堂的存在和一些敬畏上帝的希腊人在某座城市中的存在,使得建立教会的问题发生了根本变化,以至于圣保罗在这些情况下使用的方法无法应用于现代条件,那我们很可能是陷入了一种误解。会堂的存在和敬畏上帝的希腊人的出现确实使圣保罗能够吸收一些可以阅读《旧约圣经》并了解律法的人,他们对偶像崇拜或异教哲学已经感到不满,正在寻找更真实、更纯粹的教义。犹太人从小就有这种知识,成为归信者的希腊人也已经拥有了几年这种认识。但这不足以让我们认为,这些少数人的存在对教会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这些人和有这些人的教会之间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在会堂之外,圣保罗似乎并未特意针对任何特定阶层。他显然没有专门向流浪汉、搬运工、无知堕落者或街头的临时劳工传道。他也不常在街头向闲散或好奇的人群布道。尽管在路司得,那位瘸腿乞丐听了圣保罗的讲话;在帖撒罗尼迦,那位算命的女孩似乎也听过他的教导;我们还知道他曾在雅典的市集布道。然而,即使是在路司得的瘸腿者事件,也不能证明圣保罗的布道通常是在街头进行的。事实上,圣保罗的常规做法是在会堂中开始布道,然后转移到某位声誉良好的人的家中。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很小心地告诉我们,圣保罗在何处住宿以及在谁的家中教导,例如在腓立比,他住在吕底亚家并在祷告所讲道;在帖撒罗尼迦,他住在耶孙家并可能在他家中教导;在哥林多,他住在亚居拉家并在提多犹士都的家中传道;在以弗所,他在推喇奴学房教导。路加显然希望让我们明白,圣保罗在各方面都力求“行事端正”,不仅注重真理、纯洁和公正,也关注荣誉和良好的声誉。
另一方面,圣保罗并未特意试图吸引学者、官员或哲学家。他显然没有专门向这些群体布道。如果他曾在雅典对他们布道过一次,他也明确拒绝在哥林多采取这种方式。他自己说,他的皈依者中来自这些阶层的并不多。“教会最大的力量补充来自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主教莱特富特这样说。拉姆齐教授也表示:“教育与劳动结合的阶层最早受到新宗教的影响。”这种观点得到了圣保罗提到马其顿教会“极度贫困”的支持,而路加通过提到帖撒罗尼迦城“有名望的妇女”和庇哩亚城“身份显赫的妇女”的皈依,则似乎暗示有地位和重要性的男性皈依者很少。此外,书信中对奴隶的频繁提及也表明,许多基督徒属于奴隶阶层。
由此可见,圣保罗的大多数皈依者来自较低的商业和劳动阶层,包括工人、自由民和奴隶,但他并未刻意瞄准任何特定阶层。圣保罗的成功并不在于他关注某些群体,而在于他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传道。他的方法对现代传教依然具有参考价值,而并非因缺乏类似条件而无法借鉴。